天主教圣经辞典—连载31
发布日期:2025-08-09 | 作者:意鸣子天主教圣经辞典—连载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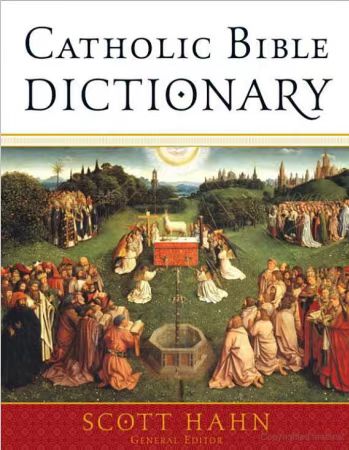
CORNERSTONE基石
基石是位于建筑物底部角落的石头。基石是建造稳定建筑的基础,因此,它在圣经中被用来比喻一个重要的个人或人物(依19:13;耶51:26;匝10:4)。在《依撒依亚先知书》28:16,上主宣布:“看,我要在熙雍安放一块石头,一块精选的石头,一块宝贵的角石作基础,信赖的人必不动摇”。保禄跟随一个流传很广的犹太传统,注释这段作为默西亚的预言。《圣咏集》118:22写道:“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在新约中,耶稣使用这段圣咏来宣告,祂自己就是新圣殿的基石(玛21:42;谷12:10;路20:17),伯多禄重申了这种联系(宗4:11;伯前2:7)。基督是圣教会的基石,圣教会是圣神的活圣殿(弗2:20;伯前2:4)。
COVENANT盟约
盟约是双方亲密关系的联结,伴随着条款制约或责任义务,建立在一个誓言或与其等效者之上。盟约在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建立和维持个人、家庭、部落甚至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盟约也是圣经的主题,记载了天主用很多方式,透过历史描绘人类藉着神圣誓约与祂自己进入一种家庭的关系。
拉丁传统中,“圣约”(Testament),未能完全呈现“盟约”的意义,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圣经是基于两个盟约,被分为两个经典:旧约和新约。尽管如此,经典的区分基于盟约,并指出了盟约的概念在圣经思想和基督徒神学中不可否认的核心。此外,为天主教徒来说,基督徒生活的泉源和高峰——感恩祭,是靠着基督的“新约”(路22:20)认定的,足以证明“盟约”对救赎计划的重要性。
I.盟约的本质和定义
“盟约”的定义引起了圣经学者们的广泛争论。特别在德国的学者们中,存在一种简化“盟约”概念为与“法律”或“职责义务”同义的倾向。契约常常包含法律或义务。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通过研究古近东的盟约,基督新教(FrankMooreCross,GordenHugenberger)、天主教(D.J.McCarthy,PaulKalluveettil)和犹太教(MosheWeinfeld,DavidNoelFreedman)的学者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实质上的共识,即盟约在本质上是一种在两个先前不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家庭关系的法律手段。哈佛的学者弗兰克·摩尔·科若思解释:一个盟约“是一个广泛的法律手段,它将亲属的义务和特权延伸到其他个人或群体,包括外国人。”这亲属或家族关系是被订立盟约仪式中的条件和义务所约束的,通常是由一个礼仪仪式组成,以一种口头或仪式上的宣誓达到高潮,由盟约的一方或双方来施行。
将盟约简单视为一种契约是不正确的,因为通常一个契约包含商品的交换,然而一个盟约包含个人的交换。不像大多数契约,盟约不仅仅是社会性的,还有神圣性的约束,这是一种用誓言来呼求天主(或者是多神论社会中的众神)执行盟约义务的方式。
II.立约的意义
圣经和众多古近东的文本描绘了在两个团体之间,用来建立或隆重庆祝盟约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几乎每一种情况下,立约的核心行为都是立约团体的一方或双方宣誓(创21:31-32,22:16;26:28;苏9:15;则16:59,17:13-19)。盟约通常以自咒(self-curse)的形式存在。立约者被天主或众神所召唤,如果他不遵守进入立约的义务,就会遭受死亡或其它严厉的处罚。这誓言可以是口头宣布,也可以用一个仪式来表达。古近东社会上的盟约内容记载有自咒的各样仪式,比如以下这个来自主后754年亚述的描写:
这不是羊的头,而是马啼依鲁(立约者)。
如果马啼依鲁违犯此盟约,
但愿如此,就像这只春天的羊羔的头被扯下来一样,
马啼依鲁的头也被扯下来。(ANET532)
一个自咒仪式是把动物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尸体中间走过去(创15;耶34)。这仪式代表的内涵是:“如果我不遵守这盟约,愿我像这些动物那样被杀死”(耶34:18)。圣经记载了其它的自咒仪式:动物的牺牲和洒血(出24:8;咏50:5),表达“如果我不遵守盟约,愿我自己被切断(杀死)”。
在圣经中其它与盟约仪式相关的仪式,并没有表达自咒,而是例证了盟约关系中的其它方面。通常订立盟约的双方是以共同进食来确定他们新的家庭关系(创26:30;31:54;出24:11;苏9:14-15;路22:14-23)。使用家庭术语(弟兄:列上:20:32-34;父亲和儿子:咏89:26-28;2:7;撒下7:14)和交换衣物(撒上18:3)或其它礼物(创21:27)也能够表达家庭的亲密关系。
新约是建立在最后晚餐之上,即立约双方之间的聚餐,类似于梅瑟和长老们在西乃山与天主共享一餐(出24:11)。换句话说,耶稣特别的表达:“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玛26:28),回应了梅瑟在西乃山立约期间洒牺牲动物血时所说过的话(谷24:8)。感恩祭既是家庭聚餐,也是新约的隆重献祭。
很多用于立约或重申盟约的仪式本质上是礼仪性的。它们是按照神圣的习俗,在天主(或众神)前来履行的,即:天主被召唤来见证和实施盟约的义务。由于天主的临在,立约仪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圣殿或圣山的神圣地点,是立约仪式的首选之地。
研究立约仪式有助于我们了解到,盟约有家庭、法律和礼仪三个幅度。简单来说,一个盟约是建立在法律约束的誓言之上,并在礼仪仪式中宣告的一个家庭约定(familialbond)。所有这一切在西乃山的盟约仪式中都是可见的(出24:3-11)。家庭约定是藉着天主和以色列长老们在西乃山的聚餐得以说明的(出24:9-11)。具有法律约束的誓言是藉着洒血之后人们庄严的一个自咒仪式(aritualself-curse)来表达的(出24:7-8),约束他们遵守在《出谷纪》20-23章宣布的所有法律的义务。一个礼仪的仪式作为宣誓的内容:在圣地祭坛上奉献祭品(出24:4-5)时,呼求上主的名(出24:7-8)。
III.盟约的分类
依据立约双方的身份,盟约可以分为两类:“人”的盟约双方都是人,然而,天主(神圣)的盟约中,天主是其中一方。
依据某个社团的宣誓建立的盟约,也可以分类:当社团双方宣誓时,一个“亲属关系”(社团关系)的盟约就形成了。这盟约类型标注的是“亲属关系”,是因为盟约的家庭性质是在关系的最前端,而不是社团中一方从属于另一方。彼此宣誓表明社团双方接受遵守盟约义务的责任,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或至少是相互的关系。圣经中一些亲属类型的盟约,包含立约仪式中的一个家庭聚餐(创26:30;31:54;出24:11)。
当下级一方独自宣誓时,是一种“臣属类型”的盟约。在这境况中,上级一方把盟约关系强加给下级一方,而下级一方常常是叛逆的仆人。古近东臣属盟约的例子,包括众所周知的厄撒哈冬臣属条约(VassalTreatiesofEsarhaddon:亚述王,约主后681-669年),就是厄撒哈冬强加给不可靠的臣属国国王,以确保他们服从自己的继承人——亚述巴尼帕耳。圣经中的例子包括《创世纪》17章的割损礼,只有亚巴辣罕履行仪式的盟约誓言;《申命纪》的盟约中,只有以色列人民使用自咒来履行遵守盟约的条款(申27:11-26;苏8:30-35)。
当上级一方单独宣誓,他与下级一方建立一个“恩赐类型”的盟约。这些“恩赐”盟约是古近东的国王们奖励忠诚的仆人经常使用的,通常是永久赐予他们一块皇家的土地(因此才有了“恩赐”这个词)。在这种盟约形式中,上级一方接受维护盟约的所有责任,而下级一方则是靠着前人的功绩。圣经中的例子包括亚巴郎盟约的最终形式(创22:15-18)和达味盟约,尤其是在《圣咏集》89:3-37中的描述。
IV.在古代和圣经中人类的盟约
在古近东的考古学中,发现一些非以色列人的盟约。这些文献中较大的两本是《赫特条约》(HittiteTreaties)和之前提及的《厄撒哈冬臣属条约》。《赫特条约》是在主后两千年,由赫特国国王和周边国家国王之间订立的盟约组成,其功能相当于古代的国际条约。这些盟约遵守规定的架构,在《申命纪》中也很明显:
1.序言(1:1-5)
2.历史的序幕(1:6-4:49)
3.条款(5:1-26:19)
4.祝福和诅咒(27:1-30:20)
5.保管和宣读的安排(31:1-34:12)
一些学者指出《申命纪》与《赫特条约》二者之间的相似的架构,作为《申命纪》可以追溯至主后两千年的论据(符合梅瑟的身份),而且古近东在主后一千年的盟约并不是同样的架构。例如《厄撒哈冬臣属条约》(主后第八世纪)忽略了历史的序幕和祝福。这些严苛的条约是被厄撒哈冬强加给其附属国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冗长和多样的盟约诅咒列表,其中一些听起来与《申命纪》28:15-68的那些内容相似。
很多两个人类社团之间的盟约被记载于圣经中:亚巴郎与阿彼默肋客(创21:22-33),依撒格与阿彼默肋客(创26:26-33),雅各伯与拉班(创31:43-54),以色列人与基贝红人(苏9:15),达味与约纳堂(撒上18:1-4;20:8),阿哈布与本哈达得(列上20:32-34),约雅达与宫廷卫队(列下11:4)等等。这么多记载于圣经中的人类盟约,证明了盟约在古代社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广泛使用。这些盟约形成了神圣的约束,即使是建立在虚假伪装或胁迫下,也是会招致诅咒的(苏9:19;则17:11-21)。
V.圣经中的神圣盟约
以色列人在古代是唯一相信天主的民族,并且他们已经进入到天主与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中。圣经是依照天主与人类之间透过不同个体的媒介(亚当、诺厄、亚巴郎、梅瑟、达味,最终是耶稣基督),所建立起的一个神圣盟约秩序而构成的。
尽管创造叙述(创1-3)并没有使用“盟约”这个词汇,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暗示或间接的指示,指出天主与受造物之间存在一个以亚当为媒介的盟约:(1)创造叙述在安息日达到了高潮,这在圣经别处(出31:12-17)是盟约的“标记”;(2)在《创世纪》6:18中,与诺厄立约所使用的动词,并不是通常启动立约的动词(希伯来语kārat),而是一个表示维持或更新现有盟约的术语(希伯来语heqim)。《创世纪》第6章与《创世纪》第1章之间相似的语言暗示,与诺厄“更新”的盟约是存在于创造中的那个盟约;(3)在《欧瑟亚先知书》6:7,先知将以色列与亚当在对盟约不忠方面相比:“他们在阿当就违犯了盟约(他像亚当一样,违反了盟约)。”
受造物或亚当盟约约束的是天主与亚当,其身份是天主之子(创1:26-25;5:1),受造物的管理者(代管者vice-regent)(创1:28)。盟约的条件是不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创2:16-17);相应的诅咒是死亡(创2:17)。
亚当和厄娃随后对盟约的破坏将死亡带进了人类历史(创4:8),并开启了一个罪恶的循环,最终需要藉着大洪水来洁净世界。大洪水之后,与诺厄更新了最初受造界的盟约(创9:1-17),并修订了条款:人与自然之间一度的和谐被破坏了(创1:29-30;9:2-6)。
天主由亚巴郎开始拯救人类的过程,是因为他是旧约中接纳盟约的最佳典型。天主与亚巴郎至少订立了两个盟约:创15:1-21和17:1-27。另外,有鉴于“誓言”与“盟约”之间密切的关系(创21:31-32;则17:13-19),很可能《创世纪》22:15-18中的神圣誓言也建立在与亚巴郎的一个盟约之上。每一个盟约都是基于先前的那个盟约,并不断增添。
在《创世纪》15章中,亚巴郎与天主之间订立了最初的盟约,因着认真履行先前的许诺,亚巴郎将成为一个“大民族”(创12:2)。《创世纪》15章中盟约的许诺包括:亚巴郎的许多后裔,并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是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民族”的必要因素。
在《创世纪》17章中,扩充早期亚巴郎的盟约,包括亚巴郎的后裔为王的一个许诺(创17:6),以及亚巴郎将成为不仅一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的期望(创17:5-6)。这也包括首次立约时割损的义务(创17:9-14)。
在《创世纪》22章,亚巴郎几乎将“独生子”(onlybegottenson)依撒格差点奉献牺牲(指向加尔瓦略山)之后,天主向亚巴郎重申了盟约誓言,但也确认了通过亚巴郎的后裔来祝福万民的许诺(创22:18),这是一个早在《创世纪》12:3中的许诺,并不包括《创世纪》15章和17章中盟约的条款。在《创世纪》22:15-18中,亚巴郎的盟约最终形成。
记载于圣经中其余的神圣盟约都是基于亚巴郎盟约。《出谷纪》中记载亚巴郎的后裔从埃及逃离,并聚集在西乃山脚下,透过梅瑟从天主那里接受一个盟约。这盟约有潜力实现给予亚巴郎的许诺:伟大的民族、王国和普世的祝福。亚巴郎的后裔显著增长,客纳罕福地就摆放在眼前,他们将接受一部法律,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大民族”的体制。
另外,最早给予的西乃盟约(梅瑟盟约)声明:对盟约的遵从将使以色列获得“王家司祭”(出19:6)的地位,就是一个司祭王国的民族,实现《创世纪》17章(众王将由你而来)和《创世纪》22:18中关于祝福万民的许诺,因为司祭的主要功能就是带来祝福(户6:22-27)。
不管怎样,亚巴郎盟约的许诺不是在梅瑟盟约下达到圆满的,因为他们立即藉着塑造金牛违犯了盟约(出32)。拜金牛事件导致以色列人重订梅瑟盟约(出34:1-35),把大司祭职委托给肋未人的长子(出32:27-29;户3:5-51),并增加了很多附加法律(出35-肋27)。增加有关旷野中叛乱的事迹(户11;12;14;16;17),尤其是在巴耳培敖耳的偶像崇拜和行淫(户25),为《申命纪》中描述梅瑟盟约的另一次更新奠定了基础。在摩阿布平原的贝耳培敖耳所宣布的(申1:5;3:29;4:44-46)差不多是在西乃事件后四十年,《申命纪》中的盟约很明显是一个独特的盟约,增加和更新了西乃盟约(也称为“曷肋布”;申29)。最初法律给予以色列人允许一个人类的君王(申17:14-20),毁灭律(全部屠杀)(申20:16-18)和离婚(申24:1-4)。耶稣后来指出,这些盟约条款中至少有一些并不是神圣的典范,而是对以色列人心硬的妥协(玛19:8-9)。
虽然以色列根据梅瑟法律的后续记载是非常多变的,但是雅威为其人民的计划在达味统治期间和撒罗满统治前期达到了高峰(撒下5:1;列上10)。达味将民族团结在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强大统治中心周围(撒下5),并使崇拜上主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撒下6-7)。天主赐予一个盟约(撒下7:5-16),然而“盟约”这个词仅仅是后来引用该事件时才出现的(撒下23:5;咏89:19-37,132:1-18;依55:3;编下13:5,21:7;耶33:20-22)。这盟约的术语使达味和其后裔成为天主的儿子(撒下7:14;咏89:26-27),统治大地的至高君王(咏89:27;2:6-9)将永享统治(撒下7:13,16),并将建立天主的居所——圣殿(撒下7:13)。
撒罗满短暂的繁荣之后,这些盟约的许诺在这期间明显实现了(列上4-10):达味的王国进入了长期的衰落,开始于以色列人分裂为北国十个支派和南国犹大(列下12)。在天主的子民分裂衰败期间,先知们宣告了一个新盟约的到来(耶31:31;依55:1-3,59:20-21,61:8-9;则34:25,37:26)绝不会如同不成功的梅瑟法律(耶31:32;则20:23-28;依61:3-4)。同时,达味的盟约也将复兴(耶33:14-26;依9,11,55:3;则37:15-28)。
四福音中,尤其是《玛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清楚地描绘耶稣是达味之子(后裔),即复兴达味盟约的那位(玛1:1-25;路1:31-33,69;2:4)。在最后晚餐中,耶稣明确认定:祂的身体和血作为先知们(耶31:31)所许诺的新盟约(路22:20;格前11:25),如此惊人地实现了依撒依亚的许诺:上主的仆人将并不单单订立一个盟约,而是成为一个盟约(依42:6;49:8)。根据《希伯来书》所述,新盟约优于旧的(梅瑟的盟约),因为是因更好的中保(基督与大司祭相比:希8:6,9:25)而建立的,也基于更好的祭品(基督的宝血与动物的血相比;希9:12,23),并在一个更好的圣所(天国自身与地上的会幕相比;希9:11,24)中订立的。
如果新盟约超越梅瑟的盟约,那么也复兴和超越达味的盟约。耶稣基督是达味之子,将永远统治天上的熙雍(希12:22-24),并藉着祂王国的管家伯多禄(玛16:18-19;依22:15-22,尤其是22节)和其他宗徒们(路22:32;玛19:28;列上4:7),来彰显祂统治以色列和万民的权柄(玛28:18-20)。因此,雅各伯宗徒将教会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成长,视为《亚毛斯先知书》中天主将复兴达味坍塌的“帐幕”(王国)(宗15:13-18;亚9:11-12)。
此外,新盟约涵盖了救恩历史中其它盟约的实现。因此,耶稣是新亚当(罗5:12-19),使我们成为一个新受造的人(格后5:17;迦6:15)。他满全了亚巴郎盟约的所有许诺(路1:68-75,尤其是72-72),包括“大民族”(圣教会;伯前2:9)、王权(默19:16)、万国之父(罗4:16-18)和圣神倾注万民使人经验到“对万民的祝福”(宗3;25-26;迦3:6-9,4-18)。至于梅瑟的盟约,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一些(迦3:19-25),因为其实质已经被新盟约所满全了,赐予信友圣神的恩宠力量已经满全梅瑟法律最核心的教导:上爱天主,下爱近人的诫命(罗8:3-4,13:8-10;玛5:17,22:37-40)。
VI.英语翻译术语“盟约”
在旧约中使用“盟约”是希伯来语单词bĕrît。古希腊语翻译的旧约《七十贤士译本》一直用希腊语单词diathēkē描绘这个术语。毫无疑问,新约圣经的圣作者采纳了《七十贤士译本》的用法,使用这个术语diathēkē来意指bĕrît(盟约)。不过,由于古希腊作家使用diathēkē指代一个“约”(testament)(awill:一个意志、心愿、遗嘱),导致一些古英语的翻译,比如英皇詹姆斯钦定版在某些段落采用diathēkē作为“约”(testament)。除了一些情况之外,更多近代的翻译纠正了这个错误。例如,希9:15-17在RSV(修订版)中全文如下:
为此,祂(基督)作了新约(covenant:diathēkē)的中保,以祂的死亡补赎了在先前的盟约(covenant:diathēkē)之下所有的罪过,好叫那些蒙召的人,获得所恩许的永远的产业。凡是遗嘱(awill:diathēkē),必需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因为有了死亡,遗嘱(awill:diathēkē)才能生效,几时立遗嘱者还活着,总不得生效。
在15节,希腊语diathēkē被翻译成“盟约”,而在16-17节被翻译成了“遗嘱”。很多人认为作者在后来的章节中转换成diathēkē的意义,讨论似乎是围绕着履行一个死者的遗嘱。然而,很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6-17节意为“盟约”。讨论中的盟约是在西乃破碎的盟约,依据《出谷纪》24:8(出32:9-10)的自咒仪式,以色列人就该死。这些希腊语章节可以这样翻译:“为此,那里引发(破碎)的盟约,就需要订立盟约者承受死亡。因此,一个(破碎)的盟约是强加给死者之上,它肯定没有生效,因为在此期间盟约制定者仍旧活着。”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强调,“破碎的”西乃盟约需要以色列人的死亡(出32:9-10),因为他们引发了订立盟约典礼期间死亡的诅咒到他们自己身上(出24:8)。当人们背离上主和朝拜金牛时(出32:14),那死亡的诅咒并未偿付,因为是基督祂自己代表以色列人最终付清了(希9:15)。
一个类似的事情出现在《迦拉达人书》3:15中:“弟兄们!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awill:diathēkē),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得废除或增订。”
以下章节就没有理由把diathēkē翻译成“遗嘱(will)”了。在这内容中(迦3:15-18),保禄讨论盟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如果人类的盟约也不能在事实发生后改变(迦3:15;苏9:18-20),那么,一个神圣的盟约当然更不可能了(迦3:17)。天主不会在四百年后(迦3:17-18)藉着增加梅瑟法律作为改变祂与亚巴郎之盟约(创22:15-18)的因素:即藉着他的后裔祝福万民(创22:18;迦3:14)。既定事实后改变盟约是不被人类正义所允许的,更何况是天主的盟约呢?
总而言之,按照《七十贤士译本》的做法,新约中所有的diathēkē可能而且应该被翻译成“盟约”。
译者:关于中文“盟约”的解读,思高圣经学会的《圣经辞典》207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