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年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光荣十字架(三篇译文)
发布日期:2025-09-13 | 作者:意鸣子丙年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光荣十字架
天国源于天主,不是来自世界。
达尼尔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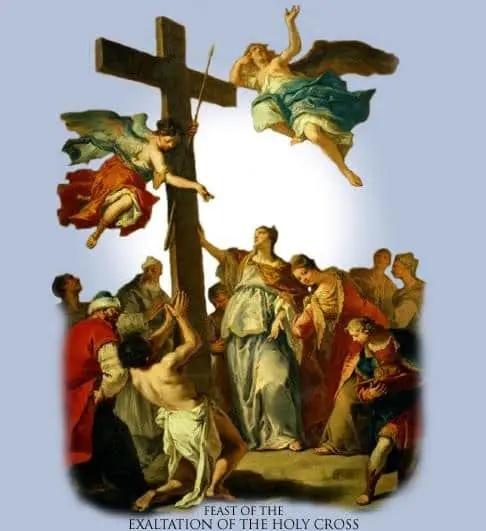
如今,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王室不过是八卦小报与漫画作品的素材罢了。
当年戴安娜王妃离世及其后续事件引发媒体广泛关注时,我们曾集体聚焦于国王与王后这类王室议题。在那次事件中,王室成了尴尬的背景板,并且再次引发了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时代,君主制及其相关仪轨是否还有实际意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光荣十字架节”这一独特的庆典呢?正是这一事件,使耶稣得以被认定为君王。
事实上,近东地区关于王权与王国的表述,是基督宗教启示的核心所在。天主的统治是耶稣布道的核心内容;而宣告耶稣为基督(即人们所期盼的“未来时代”的受傅油君王),更是我们信仰教义的核心要义。
因此,摒弃或彻底重塑这种象征意义是绝无可能的。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重新探寻圣经中关于“君王”论述的含义,并重新发现它在今日如何指导我们践行信仰。
人们之所以不愿接受这种“君王”象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耶稣同时代人对“受傅油者”(即默西亚)所关联的君王形象有关。主后1世纪的许多犹太人,似乎都在期盼一位能以达味王的方式带领民众的默西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似乎意味着带领民众发动武装起义,反抗罗马人的统治。
尽管耶稣从未渴望成为这样的默西亚,但他对圣殿领导层的质疑,仍让他们抓住耶稣关于“天主之国”的论述大做文章,以此引起罗马总督比拉多的注意。耶稣的反对者坚称:一个不断谈论“王国”、且被追随者奉为“受傅油者”的人,必然会对罗马的法律与秩序构成威胁。当然,在耶稣受难日那天,无论是犹太人对他的审问、罗马人的审判,还是士兵对他的嘲弄,核心议题都围绕着耶稣与“王权”的关系展开。
在《若望福音》的记载中,这一议题的呈现方式尤为值得关注。书中描述了耶稣与比拉多的一段对话: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就比拉多提问的意图进行简短交锋后,耶稣回应道:“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若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我的国不是这样的。”
这段对话揭示了两点核心信息:耶稣既没有拒绝“君王”这一称号,也没有认同该称号所蕴含的常规政治意义。他的王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王权;他的权柄,其力量来源也并非这个世界。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这是我们本周日(光荣十字架节)大概率会听到的译文,且译得十分贴切。但很多人自以为听到的,可能是近四个世纪以来在英语译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句译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见于1582年的《兰姆译本》与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如何翻译希腊语原文,直译为“来自这个世界”,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句话,成了某些基督徒将宗教与政治彻底割裂的“依据经文”。例如,当主教们呼吁信徒承担更多政治责任时,反对者有时会这样反驳:“宗教和经济有什么关系?耶稣不是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吗?”
在这一点上,《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天主教版)》的直译或许能有效纠正这种误解。该版本将这句话译为:“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来的……但事实上,我的国不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译本清晰地表明,耶稣的核心意图是说明“天国权柄的来源”(源于天主,而非世俗),而非“天国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的王权“不属于这世界”,“不源于这里”。
整部《新约圣经》都明确指出:对天主的统治以及耶稣王权的回应,与我们如何践行世俗公民的责任息息相关——包括我们如何工作、纳税、消费、经营,以及如何投票。
也正是在这样的践行中,我们尊崇那位“忠信的见证人,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默1:5)。
先知式的生命践行,始于脚下。
若望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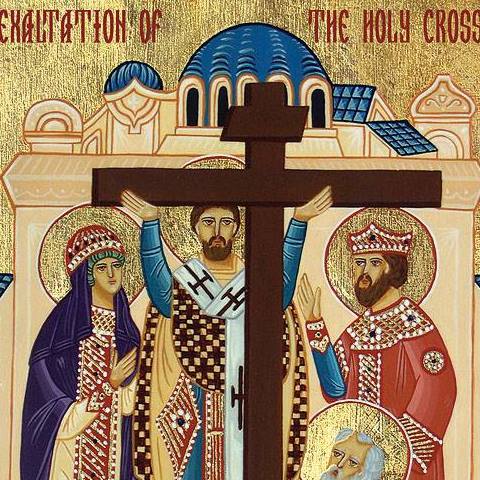
我们大多听过对“专家”的一句老调侃:凡是从五十里以外来的人,都能算专家。如今,这个距离标准恐怕得改成五百里甚至一千里了。似乎我们总对“亲近之物”“平凡日常”抱有某种排斥——越熟悉的,越难让我们信服。
人们最推崇的,是远道而来的“专业见解”;对“先知恩赐”的看法,亦是如此。在大众认知里,最好的先知总是那些来自遥远时空的人物。而“此时此地”的先知,境遇则截然不同:“她怎么可能是先知?我和她可是同学。”“他哪会说预言?我连他妈妈都认识。”“那家伙怎么能给别人带去恩宠与喜乐呢?我和他在团体里相处好几年了,他讲的笑话难听极了,还总戴法式袖扣。”难怪有人说“仆人眼中无英雄”——或许正是这种“过分熟悉”,让我们看不见身边人的先知特质。
我们排斥的不仅是身边的先知,更排斥“内心的先知”。这种排斥,本质上是压抑了我们自身最平凡、最熟悉的那个“自我”中所蕴含的先知精神与英雄气概。
我们往往最了解自己,就像仆人熟悉主人一般,因此也最怀疑自己能成为先知或英雄的可能性。在与自己最亲近、最私密的心灵空间里,我们几乎不给“预言”留任何余地;如此一来,信仰的奇迹,自然也难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
“先知在自己的故乡,除了少数人之外,是不受尊敬的。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迹,只因他们不信,他就甚是忧愁。”(谷6:4)
和历史上许多“不情愿的先知”一样,我们也常以“与自己太亲近”为借口逃避使命:“我太年轻了,准备得还不够;我年纪太大了,既软弱又有罪;我太忙了,心思根本分不开;我长得太普通,或是性格太温和,不适合做先知。要是我能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在某个未知的时刻,换个身份,凭着激昂的言辞和耀眼的美德挺身而出就好了;要是我能站上讲台,或是得到主教的垂青,甚至能在枢机团里做一名‘圣洁的颠覆者’就好了。那样的话,那样我就能行先知之事了。”
可现实中,我们总在说:“不是在这里,不是现在,也不是我。”
倘若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拒绝相信自己有成为英雄或先知的可能,根源在于我们太清楚自己的软弱与不足。我们总觉得,英雄不可能藏在如此平庸的天赋、如此普通的外表之下;先知的生命,也不该像我们这样充满失败与缺憾。
圣保禄似乎也曾被“自身不足”的念头困扰。他曾三次祈求天主,除去他“肉身中的刺”,但这份祈求似乎并未得到他所期待的回应。
然而,若我们能像圣保禄那样,学会“为基督的缘故,甘心忍受软弱”(格后12:9),或许有一天会忽然发现:自己被天主释放了束缚,心灵变得勇敢,口中的话语也变得坚定而自由。
因为圣保禄早已告诉我们: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格后12:10)
若真是如此,那么所有的先知使命,正如所有的责任一样,都始于“身边的小事”,源于“当下的践行”。
吃肉喝血,好能参与基督的奉献
福利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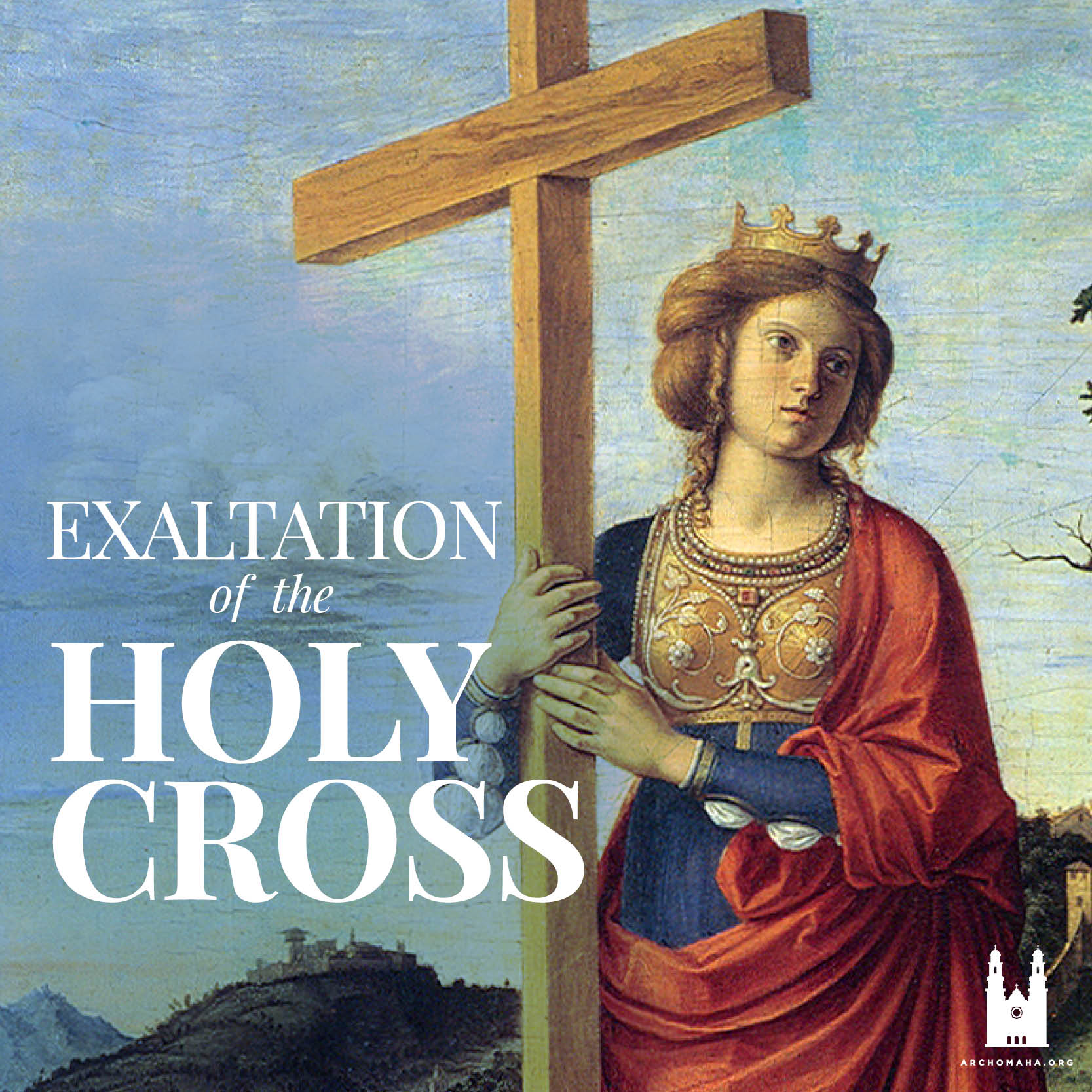
你说你们在吃某人的身体、喝某人的血?
这里有个或许不够得体的问题:为何要这样做?
“牺牲”一词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而这历史中,始终与“神圣十字架”紧密相连。
你们沿着教堂的通道走向祭台,领受那看似面饼与葡萄酒的事物——但依你们的信仰,那是基督的身体与血。正因如此,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主后23-79年)曾将基督徒描述为“食人肉者”。当年耶稣说“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若6:56)时,许多跟随他的人也直接离开了。这话确实刺耳难明。
要回答这个问题,仍需回到“牺牲”一词本身。但我所说的并非它如今常见的含义——比如四旬期里“放弃自己喜爱的事物”,或是父母常说的“我为了抚养你们,牺牲了自己的兴趣”。
“牺牲”一词的历史远比这更深远,而重要的是,它的核心始终与“十字架”相关。
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族群都会依照传统,设法取悦他们所信奉的神明。他们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求得上天免除风暴、旱灾、饥荒等灾祸。他们献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期盼能赢得神明的青睐。
而且,他们常常会将所献之物杀死!为何要这样做?
因为从羊群中选出最肥美的羔羊宰杀,才能让它成为献给神明的“至佳礼物”。无论是羔羊、鸽子(甚至在某些文化中是少女),它们都代表着世间最宝贵的事物;而死亡能将这礼物从尘世中释放,送往天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将尘世的至佳之物送往天国,好让天国的至善之恩降临尘世。
这是一种“天与地的结合”。彼时,人们常会食用所献之物的肉、饮用其血——为的是让自己成为这场“牺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种“渴望与神明合一、与神明的恩赐及美善合一”的心愿,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与人性之中。因此,在“时期满了”的时候(迦4:4),独一的天主为祂的子民预备了一条与祂自身相连的道路——不是异教所幻想的假神,而是真实的天主。正如你所料,天主是通过“牺牲”成就这一切的。但祂颠倒了以往的秩序:不是人献上礼物,而是祂亲自降临,成为那被牺牲者。
请注意这其中的差别:
以往,人们是“将尘世的至佳之物送往天国,好让天国的至善之恩降临尘世”;而天父却行了相反之事:
祂将天国的至佳之物(即十字架上的基督)送往尘世,为的是让尘世的人能升向天国。
基督来自天国,却又属于这世界。因此,是祂为我们成就了天与地的完美合一。牲畜无法选择是否成为祭品,但基督是出于爱,为了我们,自由地选择了牺牲。
因此,在祂受难的前一夜,耶稣将自己即将成就的奥迹,以圣事的记号赐给了门徒:祂以面饼和葡萄酒的外形,将自己的身体与血交给他们,并吩咐他们领受。从此,十字架上那流血的牺牲,便以不流血的方式,在所有时代中“重新呈现”。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开篇的问题了:“为何我们要吃祂的身体、喝祂的血?”从以上论述可知,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参与基督向天父所献的“牺牲”——在这牺牲中,基督将全人类都呈献给天父。祂也将我们——包括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过失、我们的健忘——都纳入这奉献之中,亲自担当一切,以爱的代价成就了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