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圣经辞典—连载46
发布日期:2025-10-11 | 作者:意鸣子天主教圣经辞典—连载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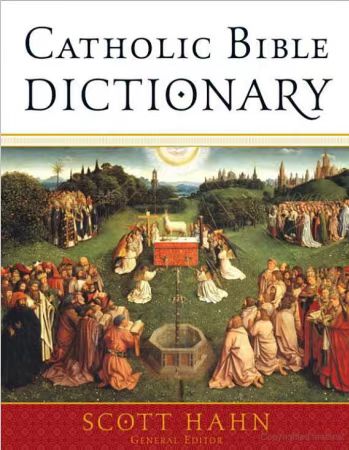
棕榈树Palm
枣椰树(学名Phoenixdactylifera)在中东地区广泛分布,从美索不达米亚横跨巴勒斯坦直至埃及。在巴勒斯坦,其生长仅限于沿海平原和约旦河谷耶利哥周边(耶利哥被称为“棕榈城”,申34:3;编下28:15)。棕榈枝是喜乐的象征(肋23:40)。当耶稣荣进耶路撒冷时,群众以棕榈枝迎接祂:“第二天,来过节的群众,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便拿了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说:‘贺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应受赞颂’”(若12:12–13)。基于此(默7:9),棕榈成为殉道者的象征之一。
纸草Papyrus
纸草是一种水生芦苇(学名Cyperuspapyrus),在埃及大量生长,约从主前3000年起被用作常见书写材料。其名称源自埃及语“河生植物”,因这种芦苇通常生长在尼罗河口的沼泽中,较少见于尼罗河岸。纸草纸的制作方法是将芦苇茎的髓切成薄片,交叉铺放后压制而成。随后将纸页首尾相连,制成可卷成卷轴的长条形纸张。纸草卷轴在地中海世界很常见,埃及通过向近东等地出口丰富的纸草贸易获利。
再来Parousia
再来是希腊术语,在圣经中意为“来临”或“临在”。有时指某人抵达某地(友10:18;斐1:26;格后7:6),另一些章节中则指某人的“临在”(区别于“不在”)(格前16:17;格后10:10;斐2:12)。更重要的是,新约作者用此术语指基督未来作为审判者的来临,或在第一代基督徒时期(玛24:3),或在时间终结时(得前4:15)。神学思考还指出,基督在历史中的来临与祂在圣体圣事礼仪中的临在相关联。
I.一世纪的再来
“再来”的一层含义在耶稣的末世论论述中展开。当耶稣以圣殿沦为废墟的异象使门徒震惊(巨大的石头被抛成毁灭的堆垒,玛24:2),他们问:“请告诉我们:何时要发生这些事?你来临和今世终结的记号是什么?”(玛24:3)耶稣以世界陷入混乱的戏剧性描述作答:祂来临的前奏将是空前的欺骗、迫害与苦难。此后,“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玛24:30)。这一伟大事件的确切日期和时辰未被启示,但耶稣指向教会最初的日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世代绝不过去,直到这一切事成就”(玛24:34)。
此类表述表明,耶稣预言了约四十年后(主后70年)罗马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对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事件——不仅超百万犹太人死亡或沦为奴隶,更以耶路撒冷圣殿被火焚毁告终,标志着梅瑟宗教以牺牲崇拜为核心的时代结束。此外,耶稣亲自扮演了促成此事的主导角色,因祂作为人子的来临,是对拒绝其默西亚宣称的这座城市的审判(玛26:63–65;路19:41–44;若19:15)。这并非肉眼可见的来临(如耶稣亲自率领罗马军队),而是基督以天国审判者身份,在灵性层面针对人的行为施行审判(玛16:27–28)。
II.最终的再来
从最早时期起,基督徒也相信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历史的最后一幕,耶稣将荣耀归来审判生者死者。这一信仰在新约中亦有根基,最经典的总结见于《宗徒大事录》:路加记载耶稣离开世界的那日,“这位耶稣,你们看见祂怎样升向天上,也要怎样降来”(宗1:11)。“以同样方式”归来的观念,暗示耶稣将以有形的身体再次来临——可见、可触、荣耀地,披着将祂带到父右边的天上云彩(宗1:9;2:32–33)。
书信中提供了关于第二次来临及相关事件的更多启示:我们得知基督将作为救主来临——当祂在主的号筒声中从天上降下时,将使死者复活(格前15:23),并聚集地上的圣人与祂永远同在(得前4:15–17)。祂也将作为神圣战士来临,击杀“不法之人”(常称“反基督者”)——这邪恶形象将在末日以恶魔般的能力欺骗不信的世界(得后2:8)。届时,现存的世界将被火净化,成为新天新地(伯后3:12–13)。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在高山上目睹祂显圣容时,曾瞥见祂来临的荣耀(伯后1:16–18;谷9:1–8)。
信徒当关注的并非预测最终再来的时间,而是为这一事件预备自己:必须耐心等待主纠正世界的不公,使心准备好迎接祂(雅5:7–8),即应在圣德中坚定自己(得前3:13),在肉身、灵魂和心神上完全成圣(得前5:23)。同时,不应因“耶稣已归来”的宣称而不安(得后2:1–2),也不应因末日出现的嘲讽者嘲笑祂似乎延迟来临而惊讶(伯后3:4)。
III.礼仪中的再来
新约从未将希腊术语“parousia”与圣体圣事或基督徒一般的礼仪崇拜直接关联,但“耶稣临在于祂的子民,并在圣体中真实临在”的观念,使早期基督徒认为这与“再来”的关联既合理又具意义。事实上,将基督在历史中的来临与祂在圣事中的临在相联结,在圣经中有坚实基础。
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真实临在”神学,基督的教导是逻辑起点。首先,耶稣在《若望福音》6:35-59中于会堂的讲论,以血肉之躯的现实主义确立了基督的人性在圣体中的临在。耶稣在强调必须信靠祂为“生命之粮”(若6:35-47)后,继而坚持信仰需通过食用这“食粮”来彰显——而这食粮正是祂的“肉”(若6:51)。祂通过反复强调作出有力宣告:耶稣呼吁领受祂的肉与血,作为永生的圣事(若6:53-58)。
祂的人性如何作为食粮赐给信徒,在最后晚餐的记载中得以揭示(玛26:26–29;谷14:22–25;路22:14–20)。此时,耶稣将犹太逾越节晚餐转化为基督徒崇拜的核心礼仪:祂祝圣饼与酒,使饼酒转化为祂的“身体”与“血”(格前11:24–25)。因此,福音虽未使用“再来”一词,却清楚表明:每次举行圣体礼仪时,耶稣都在圣体圣事中真实临在,作为真实的食物和饮品来到门徒面前。
保禄的教导证实了这一解读:关于耶稣的人性在圣事中的临在,宗徒断言圣体共融是对“基督的血”与“基督的身体”的真实分享(格前10:16);关于耶稣与圣事相关的来临,他宣告:“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直到祂来”(格前11:26)。一方面,保禄认为圣体礼仪指向基督荣耀的再来,但这并未使圣体成为“主缺席的圣事”——教会并非仅在等待祂最终来临时才举行这一仪式。当然,主必再来,且来时将作为审判者(格前4:5),但保禄知道耶稣在圣体圣事中已作为审判者来临:不按规矩领受圣体者,是“亵渎主的身体和血”(格前11:27),因此“是给自己判罪”(格前11:29)。换言之,审判者耶稣在以荣耀启示于世界之前,已在圣体中临在于世界。基督这两种真实临在,均构成祂真正的“再来”,其中圣事性的临在是对最终再来的预许。
珍珠Pearl
直到主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这种宝石才在古代世界逐渐为人所知,因此旧约未提及珍珠。新约中,珍珠被视为极具价值的事物(玛7:6)。耶稣将其价值比作天国的喜讯:“天国又好象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玛13:45)。
《致费肋孟书》PHILEMON,LETTER TO
新约中保禄最短的书信。保禄就逃跑的奴隶敖乃息摩一事致信小亚细亚的富人费肋孟,呼吁费肋孟在敖乃息摩返回时以仁慈相待。
I.作者与年代
作者在书信中三次自称保禄(费1、9、19节),大多数学者认可保禄的作者身份。
关于书信年代,学者观点不一。保禄在狱中撰写此信(第1、9–10、13、23节),但不清楚具体是哪次监禁——凯撒勒雅(宗23:31–35)、罗马(宗28:16–31)或其他地点(格后11:23)。最可能的成书时间为主后60至62年,即保禄首次被囚罗马期间。因此,《费肋孟书》与《厄弗所书》《斐理伯书》《哥罗森书》同属“狱中书信”,大概率是保禄在罗马所写。
II.内容结构
I.问候(第1–3节)
II.感恩(第4–7节)
III.为敖乃息摩求情(第8–21节)
IV.请求hospitality(第22节)
V.保禄同伴的问候(第23–24节)
VI.祝福(第25节)
III.写作目的与主题
书信致基督徒皈依者、奴隶主费肋孟,以及阿斐雅(可能是费肋孟的妻子)和教会领袖阿希颇(可能是费肋孟的儿子)。由于此信与《哥罗森书》联系密切,费肋孟及其家人很可能住在哥罗森城或附近(哥4:9,17)。信中提及敖乃息摩——一名逃离费肋孟的奴隶,在保禄监禁期间相遇并皈依基督。
保禄称敖乃息摩为“忠信可爱的弟兄”(哥4:9),并让他与提希苛一同返回费肋孟处,后者携带《哥罗森书》。敖乃息摩的名字(希腊文Onēsimos,意为“有用的”)构成巧妙双关:“以前他对您无用,但现在对您和我都有用了”(费11节)。按当时法律,主人有权严惩逃奴,尤其若奴隶可能偷窃钱财或物品(第11、18节),因此保禄恳求:“请如接纳我一样接纳他。他若有负于您,或欠您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我保禄亲手写了这话:我必要偿还——更不用说您还欠我您自己呢”(第17–20节)。
这封简短书信展现了罗马奴隶制及基督徒的回应。保禄明知费肋孟有权处死敖乃息摩,仍让奴隶回家,因为敖乃息摩必须为过错补偿,且保禄愿替奴隶偿还欠款以确保正义(第18–19节)。他挑战费肋孟作真正的基督徒,认识到其义务超越罗马帝国的严苛法律,劝勉富人宽恕奴隶,并隐晦建议释放敖乃息摩(第16、21节)。奴隶与主人的旧关系未被推翻,却得以转化——正如敖乃息摩和费肋孟不再是主仆,而是基督内的弟兄。
古代传统称敖乃息摩确实获释,后来成为主教。
《致斐理伯人书》PHILIPPIANS,LETTER TO THE
宗徒保禄所写的书信,旨在教导斐理伯人团结的必要,并感谢他们在他下狱时的善待。
I.作者与年代
几乎普遍认可宗徒保禄为《斐理伯书》的作者(斐1:1)。极少数质疑者的论据未获主流认同,虽有观点称书信部分内容可能汇编自其他书信,但内部证据(包括与《宗徒大事录》及其他书信一致的个人经历提及、文学风格,尤其是神学思想)强烈支持保禄的作者身份。书信字里行间充满温暖与推心置腹的基调,极具特色。
书信年代取决于保禄下狱的时间(1:7,13–14,16–17)。保禄多次入狱(宗16:23–40,21:32–23:30,28:30;格后11:23),可能的成书地点包括罗马、厄弗所或凯撒勒雅。鉴于保禄提及“御营全军”(1:13)、“凯撒的家人”(4:22),并预期即将到来的审判(1:26;2:24),最可能的监禁地为罗马(宗28:16,30)。若成书于罗马,年代约为主后62年。
II.内容结构
I.开篇致候(1:1–11)
II.保禄的监禁(1:12–26)
III.劝勉信友(1:27–2:18)
IV.弟茂德与厄帕洛狄托的使命(2:19–30)
V.基督徒得救的道路(3:1–21)
VI.最后劝勉(4:1–20)
VII.结语(4:21–23)
III.写作目的与主题
保禄以亲切私人的语气致信马其顿重镇斐理伯的教会,不针对特定教义或纪律问题,而是向“我可爱的”(2:12;4:1)问候、鼓励,并告知自身近况。他特别感谢他们的慷慨——斐理伯基督徒得知保禄下狱后,派厄帕洛狄托携款项探望(4:18)。厄帕洛狄托在狱中服事时患病,康复后保禄遣他返乡,并希望尽快派弟茂德前往(2:19–30)。斐理伯人在仁爱与慷慨上堪称典范(4:15–16),保禄对其盛赞不已,并应许天主的降福(4:19)。
保禄深知斐理伯人面临的迫害(1:29–30;宗16:20,21),好像是来自世俗当局。他主要关注信友间的合一,以及谦卑与仁爱的态度——这是在患难中坚持的关键。保禄以基督为至高榜样(2:1–5),其中对降生成人的描述(2:5–11)是他所有著作中最优美的段落之一:基督“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生于人间的样式”(2:7),因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天主举扬祂,“赐给了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2:9)。保禄亦以自身为效法榜样,为基督“舍弃了一切”(3:8),渴望“认识祂和祂复活的德能”,“参与祂的苦难,相似祂的死亡”(3:10)。
《斐理伯书》风格极为个人化,洋溢着充沛的喜乐。因不针对具体问题,结构比其他保禄书信更松散。在自由的笔调中,读者得以窥见保禄的生命、思想,以及他对斐理伯教会深挚的情谊。
宗座圣经委员会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1902年10月30日,教宗良十三世通过宗座书信《警觉》(《Vigilantiae》)设立了一个宗座委员会。其明确宗旨为:推动天主教圣经研究,抵制圣经学术中的谬误,并研究及回应可能出现的问题。
该委员会最初由教宗任命的一小群枢机组成,并配有一群顾问,主要是来自各国的天主教圣经学者(多数在罗马宗座大学任教)。20世纪初,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世界各地提交的问题发布“答复”(Responsa)。其中较著名的涉及:历史书叙事(1905年)、对《梅瑟五书》的作者身份(1906年),以及《创世纪》前三章的历史真实性(1909年)。此时委员会的核心关切之一,是抵制现代主义思想的兴起。
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前的岁月里,这些答复推动了严肃且负责任的圣经研究,尤其在教宗庇护十二世(《由圣神嘘气》,1943年)通谕发布后。委员会1964年关于福音历史真实性的训导(《至圣教会之母》),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1965年)产生了一定影响。
1971年,教宗保禄六世为圣经委员会的组织与职能制定了新规范。首要变革是调整成员构成,以圣经学者(而非仅枢机)为主要成员;其次,委员会隶属于信理部。如今,圣经委员会主席由信理部部长枢机担任,成员仅限二十位来自不同学派与国家的学者,从以“学识、审慎及对教会训导权的天主教认同”著称者中遴选。
1971年以来,委员会发布的各类文件包括:《Fede e cultura alla luce della Bibbia》(1981年,《以圣经之光看信仰与文化》)、《Bible et Christologie》(1984年,《圣经与基督论》)、《Unité et diversité dans l’Eglise》(1989年,《教会内的合一与多元》)、《L’interprétation de la Bible dans l’Eglise》(1993年,《教会内的圣经诠释》),以及《Le peuple juif et ses Saintes Ecritures dans la Bible chrétienne》(2001年,《基督宗教圣经中的犹太民族及其圣书》)。(译注:没有找到这些文件的中文官方翻译,文件名称翻译为AI翻译。)
赞美Praise
《天主教教理》将“赞美”定义为“最直接承认天主是天主的祈祷形式。它为天主本身而颂扬祂,给予祂荣——这超越祂所行的一切,只因为‘祂是’”(《天主教教理》2639)。赞美包含其他祈祷形式,并将它们指向我们所爱的对象、所钦崇与感恩的对象:“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而我们也归于他;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格前8:6)。圣经充满对天主的赞美,从创世的首篇记载(创1:1-2:4)便已开始。天主的创造工程在喜乐与赞美中回响(约38:4-7;默4:6-11)。
因天主赐予的生命,所有人都当献上赞美。人受造是为了因天主丰盛的工程而喜乐,并承认祂的美善(编上29:10-13;咏90:14-16;斐4:4)。在以色列的节期与献祭礼仪中,“因上主而喜乐”是核心要素(肋23:40;户10:10;申16:11-12;咏42:4),其表现形式包括歌唱、舞蹈与音乐(出15:20;撒下6:14;咏149:3,150:4)。当赞美渗透于天主选民的日常生活时,其属灵意义便达至圆满:“我要时时赞美上主,祂的赞美永在我口中”(咏34:1)。
对蒙恩见证耶稣救恩大能的人而言,“赞美”是得医治或洁净后的常见回应(谷2:12;路18:43)。同样,《宗徒大事录》中,得医治或遇见福音的人也以赞美为回应(宗2:46-47,3:8-9,4:21,11:18,13:48,16:25;弗1:13-14)。早期基督徒在圣殿中赞美(路24:53;宗3:1),咏唱圣咏(弗5:19;哥3:16),同时发展出新的赞美形式——包括为耶稣的救恩、死亡与复活而作的圣歌与颂词(哥1:15-20,3:16;格前14:26;斐2:6-11;弗5:14;弟前3:16;弟后2:11-13)。同样,“光荣颂”成为深刻的赞美方式(罗11:36,16:25-27;犹24-25),其高峰在《默示录》中显现——天国礼仪的歌声常在此回响(默4:8-11;5:9-10)。
赞美与牺牲紧密相连(咏119:108;欧14:2)。基督献上了为赞美天主荣耀的至高牺牲(玛11:25-26;谷14:22-23,26;若17:1-2)。因此,教会将感恩祭作为赞美与感恩的首要牺牲:“感恩祭——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圣事——也是为创造工程而感恩的赞美牺牲。在感恩祭的牺牲中,受天主爱的整个受造物,借着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被呈献给圣父。教会借着基督,能为天主在创造与人类中所造的一切美善、公正之物,献上感恩的赞美牺牲”(《天主教教理》1359条;2639-2643)。
《箴言》BOOK OF PROVERBS
《箴言》是旧约智慧书之一,收录归于撒罗满及其他人物的格言集,内容涵盖智慧本质、行为准则、邻人责任及日常事务等主题。希伯来文名称为mišlešelōmōh,意为“撒罗满的箴言”,源自《箴言》1:1。七十贤士译本题为paroimiai,武加大译本称Liber Proverbiorum,英文标题“Proverbs”由此而来。
I.作者与年代
《箴言》是不同时期多来源汇编的智慧语录集。书中开篇将合集归于撒罗满王,《箴言》10:1再次提及此点。撒罗满之名体现其在智慧传统中“最伟大智者”的地位——据《列王纪上》4:32记载,他被认为写有三千箴言。但书中明确表示,撒罗满并非唯一作者,其内容汇集了多位以色列智者与经师的言论。书中智慧材料大多(若非全部)可追溯至充军前时期,最古老部分为《箴言》10:1–22:16所载的“撒罗满箴言”。不过,合集的最终编辑可能完成于主前5世纪。
II.内容结构
I.智慧的重要性(1:1–9:18)
II.撒罗满的箴言(10:1–22:16)
III.智者的箴言(22:17–24:22)
IV.更多智者的箴言(24:23–34)
V.更多撒罗满的箴言(25:1–29:27)
VI.阿古尔的格言(30:1–33)
VII.肋慕耳的格言(31:1–9)
VIII.贤妇赞(31:10–31)
III.目的与主题
《箴言》的宗旨在其开篇(箴1:2-6)便有阐述。此书旨在传授智慧生活的教训,故反复将智慧的实践与愚昧的生活相对比。这些箴言与智慧格言为生活提供了全面而实用的哲学。其内容涵盖诸多主题,包括正义、仁爱、自律、饮酒、懒惰、审慎,以及寻觅贤妻等。
第一部分(箴1:1-9:18)强调智慧的重要性,作为对求学者的入门引导。凡追求智慧之路、避开愚昧陷阱者,将得长寿、财富、喜乐与尊荣的回报。经文中将道德与灵性如此优美地结合,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圣者是明智的起点”(9:10)。
《撒罗满的箴言》(10:1-22:16及25:1-29:27)无明显的组织结构,但其主题常重复出现:智者与愚者的对比。据称,撒罗满的这些箴言是由犹大王希则克雅的经师收集而成(25:1)。
《智者的箴言》(22:17-24:22及24:23-34)涵盖多样主题,包括关怀穷人、教养子女、节制与贞洁。其中22:17-23:11与埃及阿孟摩普的语录有显著相似之处;而23:12-24:34的第二组语录则特别强调勤劳的必要、对邻人的诚实,以及对抗恶人。
《阿古尔的格言》(30:1-33)是一位不知名者的智慧导师,他被称为雅刻的儿子;而《肋慕耳的格言》(“他母亲教给他的”,31:1-9)则告诫智者避开情欲与酗酒。
《贤妇赞》(31:10-31)是一首离合诗,每节以希伯来字母依次开头,象征完整。此部分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呼应1-9章中的“智慧女士”形象,却以真实女性的形态呈现。诗中描述“有价值的妇人”及其美德:妻子更应因虔诚、机智、勤劳、智慧与仁爱而被珍视,而非因魅力或美貌(31:30)。《箴言》亦警告远离放荡的女人或外邦女子,因淫妇可能使人丧命(5:3-5;6:24-35;9:13-18)。这些箴言反映出父母在传递宗教价值观与智慧上的重要性(1:8;13:1;31:1)。
罪SIN
神学家将罪定义为违背天主法律的思想、言语或行为。圣奥思定的名言将罪概括为“所说、所做或所渴望的一切,凡与永恒法律相悖者”(《驳福斯图斯》22.27)。
I.定义
罪首先且首要的是因缺乏爱而冒犯天主,同时也是违背理性、真理与良知的行为;它往往也包含对邻人的不爱。无论何种情况,罪都会破坏人际关系——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天主之间。旧约将罪描述为对盟约的破坏,而盟约本是为使上主与其子民在家族式的合一中紧密相连。新约则揭示耶稣基督如何前来修复罪所造成的伤害,并使人类大家庭与天父重新和好。
II.旧约中的罪
A.术语
旧约中最常见的“罪”的术语是“ḥāṭā’”,意为“偏离目标”。它可描述民族或支派间契约的破裂(民11:27)、对亲属应尽义务的违背(创31:36)、仆人对主人的不忠(撒上19:4),或附庸对盟约宗主的反叛(列下18:14)。另一个重要术语是“’āwôn”,既指“不义”,也指由此产生的“罪债”(创15:16;撒上25:24)。还有“peša’”,表示对更高权威的故意“反叛”(列上12:19;列下8:20)。
B.神学内涵
先知们谴责罪是对天主的公然反叛(依1:2;耶2:29;欧7:13)。这并非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简单分歧,而是对天主的个人冒犯——天主召叫人在盟约的纽带中与祂建立亲密的共融(咏51:4)。事实上,罪本质上是未能如盟约所要求的那样爱天主与近人(肋19:18;申6:4-6)。因此,罪的悲剧可比作不忠的妻子背叛丈夫,将爱意转向他人(耶3:1-14;欧1:2;3:1;4:1-19)。尽管圣经中的天主超越万有,不受人类情感束缚,但经上仍说祂为百姓的不顺从而忧伤悔恨(创6:6;撒上15:35;依63:10)。
《创世纪》明确指出,罪始于创造之初。并非说罪是受造界的一部分,或天主对罪的首次出现负有责任,而是当初祖夫妇在伊甸园中背离天主时,罪进入了世界。最初的人亚当和厄娃虽沐浴在恩宠中,与上主建立了友谊,却屈服于魔鬼的诱惑(创3:1-6),违背了原始盟约(创2:16-17)。这就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人的羞耻(创3:7)、痛苦(创3:16-19)以及与天主的分离(创3:23-24)。
堕落的影响贯穿历史。其最明显的结果是神学家所说的“原罪”——人性的堕落状态,这种状态倾向于犯罪,并被剥夺了天主的恩宠。这并非亚当和厄娃后代的个人过失,但它仍是一种受损的状态,传递给历史上的每一个人。因此,罪通过人类的繁衍扩散至整个世界。《创世纪》后续章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亚当之后的最早几代人中,就已出现手足相残(创4:3-8)、一夫多妻(创4:19)、复仇(创4:23-24)和无法遏制的暴力(创6:11)。即使洪水洁净了充满邪恶的人类,也无法根除人心中的罪恶(创8:21)。数世纪后,圣咏作者仍看到罪在人类处境中的蔓延:“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咏51:5)(《天主教教理》386-409)。
III.新约中的罪
A.术语
新约中用多个希腊术语描述罪的奥秘。最常用的动词是“hamartanō”,意为“偏离目标”,在神学意义上指任何违背天主的行为(路15:18;罗3:23)。与之相关的名词“hamartia”可指被禁止的行为(玛12:31;雅1:15)、人内心倾向于此类行为的欲望(罗7:8、23)、此类行为导致的罪债(谷2:5;格前15:17),或一般意义上的不法(若一3:4)。仿照希伯来文,它也可简指“赎罪祭”(格后5:21)。其他表示罪的术语包括“paraptōma”(意为“过犯”,玛6:14;罗5:16-18)和“parabasis”(意为“违背”,罗4:15;迦3:19)。
B.神学内涵
新约的核心信息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拯救罪人”(弟前1:15)。这是祂降生成人的理由,也是祂治愈、教导并奉献生命作为牺牲的使命根基。就连祂的名字“耶稣”,也是希伯来文“yěhôšua‘”(意为“上主拯救”)的缩写,表明祂来是“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玛1:21)。
新约在旧约启示的基础上,承认罪的普遍性。耶稣指出人通常是“邪恶的”(玛7:11),保禄则宣称“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天主的光荣”(罗3:23),意思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受罪恶权势的辖制(罗3:9)。罪的首要肇事者——与妻子一同将罪带入世界的人——是最初的人亚当,他的悖逆为后世子孙留下了灾难性的遗产(罗5:12-21)。此后,人类生而成为“愤怒的子女”,需要天主的怜悯(弗2:3)。
个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撒旦对人类的危害至今仍如亚当时代一样。它暗中活动,诱惑人背叛基督(路22:2-3)、欺骗圣神(宗5:3)。魔鬼在未得救赎的世界中得逞,辖制“悖逆之子”的生命(弗2:2),使他们成为自己罪恶意志的奴隶(若8:34、44)。信徒也无法免疫于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也是撒旦攻击和诱惑的目标(弗6:12;伯前5:8)。
另一方面,人仍有自由抵抗魔鬼(雅4:7),但需与肉体——即人性中倾向于罪恶和自私的堕落欲望——进行激烈斗争(迦5:16-21)。邪恶的欲望并非都来自外部,往往源于人内心深处(玛15:19);除非人抵制这些诱惑,否则欲望会滋生罪恶(雅1:14-15)。保禄称这种内在的败坏为“罪恶的法律”(罗7:25),并哀叹它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罗7:7-24)。天主教传统称之为“贪欲的法律”。
正是这种困境,耶稣基督前来补救。祂是唯一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因为祂本身毫无罪过(格后5:21;伯前2:22;若一3:5)。魔鬼曾试图使基督背离天主,却未得逞(玛4:1-11;路4:1-13;希4:15)。相反,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摧毁魔鬼的作为(若一3:8)。祂以无瑕的牺牲,为全人类的罪赎罪(若1:29;希2:17;若一2:1-2)。基督所赚得的罪赦,通过圣洗圣事(宗2:38)、圣体圣事(玛26:28)、忏悔圣事(若20:23)和病人傅油圣事(雅5:14-15)分施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