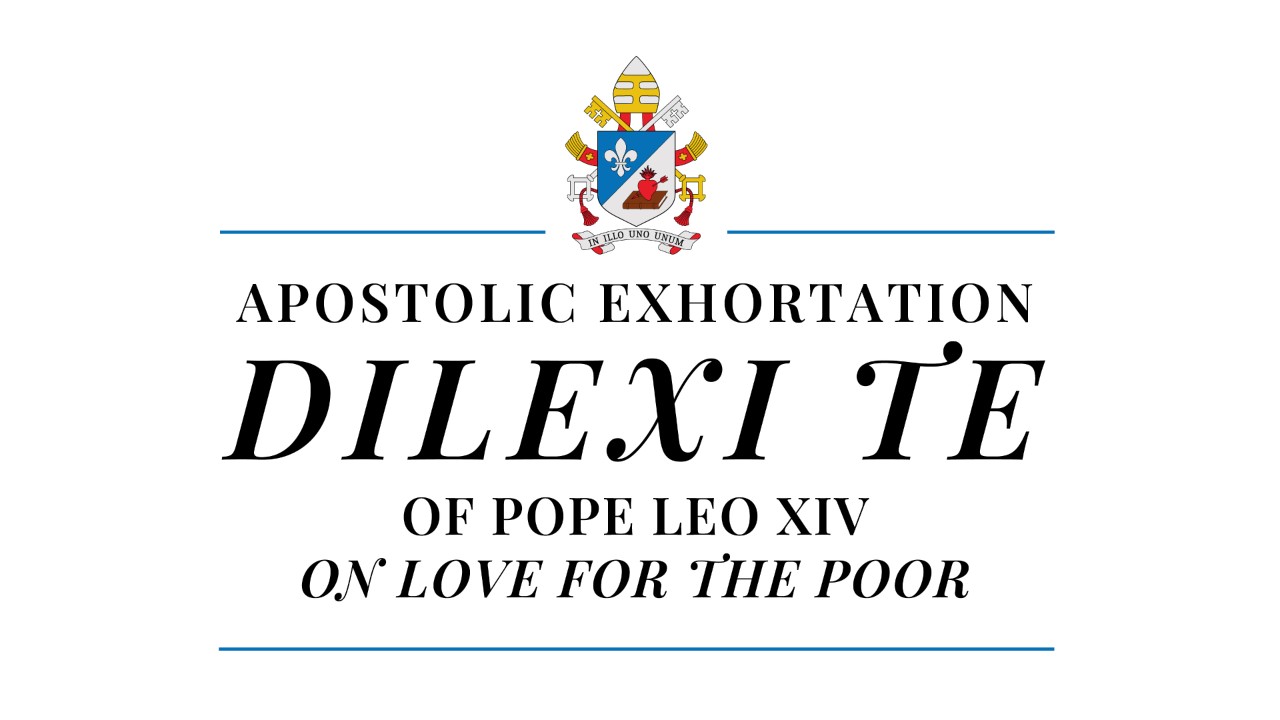《我爱了你》宗座劝谕 连载 第三章
发布日期:2025-10-15 | 作者:大海翻译《我爱了你》(Dilexi Te)
论对贫困者的爱
——教宗良十四世——
第三章 为穷人的教会
35.我的前任在当选三天后,向媒体代表表达了他的渴望:愿教会更清晰地彰显其对贫困者的关怀与顾念——「啊!我多么渴望一个贫穷的、并为穷人服务的教会!」[19]
36.这一渴望反映了教会的如下意识:她「在穷人和受苦者身上,认出她那贫穷而忍辱的创立者的肖像,竭力救济他们的贫乏,并在他们身上努力服事基督。」[20] 事实上,教会既蒙召肖似这些最微末者,那么在她内「就不应存有任何疑惑,也不容有任何淡化这清晰讯息的解释……必须毫不含糊地申明:我们的信仰与穷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结。」[21] 关于此点,在耶稣门徒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拥有丰富的见证。[22]
教会真正的财富
37.圣保禄指出,在新生的基督徒团体信众中,「按血肉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格前1:26)。然而,尽管自身贫乏,早期的基督徒仍清楚意识到,必须援助那些遭受更大剥夺的人。早在基督信仰的黎明时分,宗徒们便为七位由团体拣选的人覆手,在某种意义上将他们纳入自己的职分,设立他们专务服务——希腊文称作 diakonía——即服事最贫困者(参宗6:1-5)。极具深意的是,首位以倾流鲜血为基督作证的门徒,正是属于此团的圣斯德望。在他身上,服务贫乏者的生活见证与殉道合而为一。
38.两个多世纪后,另一位执事将以类似方式,表达他对耶稣基督的归顺,将服务穷人与殉道结合于一生之中,他就是圣老楞佐。[23] 从圣安博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老楞佐在教宗西斯笃二世任内担任罗马的执事,当罗马当局强迫他交出教会的财宝时,「次日,他将贫困者带来。当被问及他所承诺的财宝在何处时,他指向那些贫困者,说:『这些就是教会的财宝。』」[24] 叙述此事时,安博诘问:「基督还有什么财宝,能比祂亲口所言祂临在于其内的那些人更为宝贵呢?」[25] 并且,他忆及教会的圣职人员绝不可忽视对贫困者的照顾,更不应为私利积聚财物,进而断言:「我们每人都必须以真诚的信德和睿智的远见履行此义务。无疑,若有人转挪任何财物为己用,那是罪孽;但若施予穷人,若赎救被掳者,那便是慈悲。」[26]
教会教父与穷人
39.自最初几个世纪起,教会教父便承认在穷人身上有一条通向天主的特权途径,一种与祂相遇的特殊方式。对贫乏者的爱德,并非仅被视为一种道德德行,而是对降生成人之圣言的信德的具体表达。信友团体在圣神德能的支撑下,深深植根于亲近贫困者之中——他们在教会内绝非附庸,而是其活身体的核心部分。例如,在奔赴殉道的途中,安提约基的圣依纳爵就曾劝勉斯米纳团体的信友们,切勿忽略对最贫乏者履行爱德的责任,并警告他们勿效法那些与天主为敌之人:「请看看那些对降临于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恩宠持有异见的人——他们是何等反对天主的旨意!他们不关心仁爱,不关心寡妇,不关心孤儿,不关心受压迫者,不关心被囚者或被释者,也不关心饥渴者。」[27] 斯米纳的主教圣博利加则特别嘱咐教会的圣职人要照料贫困者:「长老们也应富有同情心,对众人慈悲。领回迷途者,探望一切患病者,勿忽略寡妇、孤儿和穷人,反而要时常在天主与人前,热心行善。」[28] 由此二见证,我们可见教会呈现为穷人之母,一个接纳与正义的所在。
40.另一方面,圣犹斯定在其致哈德良皇帝、元老院及罗马人民的《首篇护教书》中阐明,基督徒将他们所能及的一切带给贫乏者,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基督内的弟兄姐妹。在记述「一周首日」的祈祷聚会时,他强调:在基督徒礼仪的核心,对天主的钦崇与对贫困者的关怀绝不可分离。事实上,在庆典的某一特定时刻,「凡有资财且自愿者,各按己意奉献所认为适宜之物,所收集的则呈交主持者。他遂将其分施于孤儿寡妇、因疾病或其他缘故而陷于匮乏者、被囚者、过往的客旅——总之,他成为一切赤贫者的供应人。」[29] 如此,便见证了初生的教会从不将信与社会行动割裂:正如雅各伯所训诲,没有行为相随的信德,便被视为是死的(参雅2:17)。
圣金口若望
41.在东方教父中,或许最为热切宣讲社会正义者,当属四至五世纪间的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圣金口若望。在他的讲道中,他力劝信友们要在贫乏者身上认出基督:「你愿尊崇基督的圣体吗?那就勿容祂在祂的肢体——即那些无衣蔽体的穷人——身上受轻蔑。勿在此殿宇内以绸缎服饰尊崇祂,却在外面任祂受冻裸裎……在殿宇内,基督的圣体无需锦袍,而需纯洁的心灵;但在穷人身上,祂需要我们全部的照料。因此,让我们学习深思并按祂所愿的方式尊崇基督。当我们愿尊崇某人时,应献上他所喜悦的尊荣,而非我们所偏好的……同样,你也应按祂亲自吩咐的方式向祂献礼:将你的财富分施于穷人。天主不需要金制器皿,而需要黄金般的心灵。」[30] 他明澈地断言,若信友们未能在他们门前的穷人身上找到基督,他们在祭台上也寻不见祂,并进而说道:「归根结底,若基督在穷人身上正饥馑待毙,用金器装饰基督的餐桌又有何益?先给饥饿者食粮,而后再用所余点缀祂的餐桌。」[31] 由此可见,他亦将感恩祭理解为那先行、伴随并应在对贫困者的爱与关怀中延续的爱德与正义的圣事性表达。
42.因此,爱德并非一条可供取舍的途径,而是真实敬礼的准绳。金口若望曾痛斥与对穷人冷漠共存的过度奢华。对贫困者应尽的关怀,远非仅是某种社会要求,实是得救的条件,这使不义的财富背负遭谴的罪责:「天寒地冻,穷人衣衫褴褛地躺卧,濒死冻僵,牙关战栗,其状其貌本应触动你心。而你,却暖衣饱食,酣醉而过。你怎能期望天主救你于不幸?……你常以诸多华美金缕衣装饰那已无知觉、不复感受尊荣的尸身。却轻忽那正感受痛苦、身心破碎、备受饥寒煎熬者,你所挂虑的,竟是虚荣甚于敬畏天主。」[32] 这种深厚的社会正义感,促使他断言:「不施予穷人,即是抢夺他们,即是剥夺他们的性命,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本属于他们。」[33]
圣奥思定
43.奥思定曾以圣安博为灵修导师,而圣安博曾坚决强调「分享财富」的伦理要求:「你施予穷人的,并非你之所有,而是他之应得。因为你所侵占的,本是供众人共享之物。」[34] 在这位米兰主教看来,赒济乃是「正义的恢复」,绝非居高临下的施舍。在他的讲道中,慈悲具有先知性的特质:它抨击积攒财富的结构,并重申共融作为教会的圣召。
44.受此传统熏陶,这位希波的圣主教继而教导「对穷人优先的爱」。作为一位警醒的牧者与一位见解超凡的神学家,他领悟到真正的教会共融亦体现于财富的共享之中。在其《圣咏释义》中,他提醒信众,真正的基督徒从不忽视对最贫困者的爱:「若你的弟兄有所需要,当看顾他们;若基督居於你们内,即便是外方人,也当施予。」[35] 由此可见,这种财富的分享源於超性的爱德,其终极目的在於爱慕基督。对奥思定而言,穷人不仅是「受助者」,更是「主的圣事性临在」。
45.这位恩宠圣师视「关怀穷人」为「信德真诚与否的具体考验」。凡自称爱天主却不怜悯贫乏者,便是说谎(参若一4:20)。在诠释耶稣与富少年的相遇,以及「将财富施予穷人者将在天积攒财宝」(参玛19:21)时,奥思定借上主之口说出以下话语:「你给了我尘世之地,我将赐你天国;你给了我暂世之物,我将回赠永恒之善;你给了我食粮,我将赐你生命……你给了我栖身之所,我将赐你天乡。你在我病中探望了我,我将赐你康健。你在我囹圄中探望了我,我将赐你自由。你施於我贫困子民的食粮会被消耗殆尽;而我将要赐予的食粮,却使人力量复原,永无枯竭。」[36] 至高者在慷慨上绝不会被那些在至贫者身上服事祂的人胜过;对穷人的爱越深厚,来自天主的赏报便越丰硕。
46.这种以基督为中心且深具教会意识的眼光,使人确信:当奉献源於爱时,它不仅缓解弟兄的困窘,更「净化施予者的心,使其准备归依,『因为若你生活革新,赒济能为你赎补前愆。』」[37] 可以说,赒济是意愿以未分割之心追随基督者的「常规归依途径」。
47.在一个「认基督的容颜於穷人身上,视世间财富为爱德工具」的教会内,奥思定的思想仍是一盏确凿的明灯。今日,忠於奥思定的教导,不仅需要研读其著作,更需要「以彻底的精神,活出他那包含爱德服务的归依召唤」。
48.东西方教会的许多其他教父,都曾申明「优先关怀穷人」在每位基督徒生活与使命中的首要地位。总而言之,关於此点,我们可以断言:教父时期的神学是重实践的,它指向一个「贫穷并为穷人服务」的教会;它提醒我们:只有当福音切实「触碰到最卑微者的血肉」时,才算是善传了福音;并告诫我们:缺乏慈悲的教义严苛,只是空洞的言辞。
关怀病患
49.基督徒的慈悲,在看顾病患与受苦者方面,展现出独特的表达。基于耶稣公开传教中治愈盲者、癞病人及瘫子等标记,教会将看顾病患视作其使命的重要部分,因她易于在他们身上认出被钉的主。当圣西彼廉(San Cipriano) 所在的主教座城迦太基(Cartago) 瘟疫肆虐时,他提醒基督徒看顾染病者的重要性,并断言:「这场看似如此可怕且致命的瘟疫,考验着每个人的正义,审察着人们的心灵,查验健康者是否照料病患,亲属是否真诚相爱,主人是否怜悯患病的仆役,医生是否不离弃哀求的病人。」[38] 基督徒探望病患、清洗其伤口、安慰忧苦者的传统,绝非仅是慈善善工,而是一项教会行动——藉此行动,教会成员在病患身上 「触摸基督受苦的肉体」 。[39]
50.十六世纪,圣若望·天主(San Juan de Dios) 在创立以其名命名的医院修会(Orden Hospitalaria) 时,建立了模范医院,接纳所有人,无论其社会或经济地位。他著名的呼喊「弟兄们,行善立功!」成为了对病患践行积极爱德的格言。同时代的圣嘉祿·雷理斯(San Camilo de Lelis) 创立了病人之仆修会(Orden de los Ministros de los Enfermos)(即嘉祿会士),以全然奉献服务病患为己任。其会规要求:「每人都应恳求上主赐予恩宠,能对近人怀有慈母般的心肠,以便能以全备的爱德,在灵魂与肉身上服事他;因为我们渴望——藉天主的恩宠——以慈母照料其独一病儿时所怀的同样情感,去服事所有病患。」[40] 在医院、战场、监狱与街头,嘉祿会士们具体活出了基督医师的慈悲。
51.以慈母般的疼爱看顾病患,如同母亲照料其子女,许多献身女性在贫困者的医疗照护中扮演了更为广泛的角色。圣云先·保禄的仁爱女修会(Hijas de la Caridad de San Vicente de Paúl)、医院修女会(Hermanas Hospitalarias)、天主眷顾小婢女会(Pequeñas Siervas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 以及众多其他女修会,成为医院、安养院与长者之家中的慈母般且不显的临在。她们带去医药、倾听、陪伴,尤其是温情。她们常亲手在缺乏医疗服务的地区建造医疗设施。她们教导卫生,照料分娩,以自然的智慧与深厚的信德施药。她们的会院成为尊严的绿洲,无人被拒于门外。慈悲的触摸乃首要良药。圣路易丝·玛利拉克(Santa Luisa de Marillac) 曾致书其姊妹——仁爱女修会的修女们,提醒她们「从天主领受了特殊的祝福,为在医院中服事贫困的病患」。[41]
52.今日,这一遗产仍在天主教医院、边缘地区的医疗站、丛林中的医疗传教站、吸毒者收容中心以及战地的野战医院中延续。基督徒在病患身旁的临在,揭示救恩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行动。在清洗一个伤口的动作中,教会宣告:天主的国始于最脆弱者中间。如此行事,她便持守于那位曾言「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玛25:35,36)者之忠信。当教会跪伏于一位癞病人、一名营养不良的孩童或一位无名的临终者身旁时,她便活出了其最深的圣召:在吾主容颜最受损伤之处,爱慕主。
隐修传统中对贫困者的关怀
53.诞生于沙漠静默中的隐修生活,自始便是共融团结的见证。隐修士们舍弃一切——财富、名望、家庭——不仅出于「轻看世俗」(contemptus mundi),更为在此彻底的神贫中,遇见那位贫穷的基督。圣巴西略(圣大巴西略,San Basilio Magno) 在其《会规》中,未见隐修士的祈祷与收心生活与为贫苦者行动之间有何矛盾。对他而言,款待远人与看顾贫乏者,实为隐修灵修不可或缺的部分;隐修士即便已舍弃一切、拥抱贫穷,仍应以劳作扶助更贫困者,因「为能赒济贫乏者,我等显然必须勤勉劳作……此种生活方式,不仅为克制肉身有益,更为爱顾近人有益,好使天主藉我们之手,为较软弱之弟兄供应所需。」[42]
54.他在其主教座城凯撒勒雅(Cesarea) 兴建了一处名为「巴西利亚德(Basilíades)」的场所,内含为贫病者而设的居所、医院与学校。由此可见,隐修士不仅是苦修者,更是服务者。巴西略以此表明:欲亲近天主,必先亲近穷人。具体的爱乃是圣德的准绳。祈祷与看顾、默观与治愈、书写与接待——皆为对基督同一爱恋的表达。
55.在西方,圣本笃(诺尔西亚的,San Benito de Nursia) 制定的《会规》,成为欧洲隐修灵修的基石。其中,接待贫苦者与朝圣者享有殊荣:「对待贫苦者与朝圣者,尤当倾注格外热忱的关怀,因正是在他们身上,我们尤其接待基督。」[43] 此非空言:数个世纪以来,本笃会隐修院始终是寡妇、弃儿、朝圣者与行乞者的避难所。对本笃而言,团体生活乃是爱德的学校。手工劳作不仅具实用价值,更为陶冶服务之心。隐修士间的共享、对病患的关怀、对最脆弱者的倾听,皆为迎接那藉贫苦者与异乡人之形而来的基督作准备。本笃式的隐修款待精神,至今仍是教会敞开门户、不问缘由地接纳、不求回报地治愈的标记。
56.历时既久,本笃会隐修院成为抗衡排斥文化的场所。隐修士们耕种土地、生产食粮、配制药物,并质朴地供给最贫乏者。他们静默的劳作,成为新文明的酵母——在此文明中,穷人并非「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待接纳的弟兄姊妹」。共享、共劳、扶助弱势者的准则,构建起一种共融的经济,与积攒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隐修士们的见证表明:自愿的贫穷绝非悲惨,而是通向自由与共融之路。他们不仅援助穷人,更亲近他们,在同一位主内成为弟兄。在斗室与回廊中,一种「于微贱者身上体认天主临在」的神修得以孕育。
57.除物质援助外,隐修院在最卑微者的文化及灵性培育上亦扮演关键角色。于瘟疫、战乱或饥馑时期,隐修院是贫乏者寻获食粮与药物之处,更是寻获尊严与圣言之处。于此,孤儿得受教育,学徒获得培训,农夫学习农耕技艺与读写。知识被视为恩赐与责任而分享。院长同时是导师与父亲,而隐修院学校则成为藉真理获得释放之地。诚如若望·伽贤(Juan Casiano) 所载,隐修士当以「心灵的谦卑……为特质——此谦卑不致产生那「使人膨胀的学问」,而产生那「藉爱德的全备而光照人灵」的学问。」[44] 藉着塑造良心、传递智慧,隐修士们促生了一种基督徒的包容性教育。为信仰所浸润的文化得以朴实地分享。当知识为爱德所照亮时,便转化为服务。如此,隐修生活彰显其作为一种圣善的处世之道,以及一种具体的社会转化模式。
58.故此,隐修传统教导我们:祈祷与爱德、静默与服务、斗室与医院,共同编织成同一灵性肌理。隐修院是聆听与行动、钦崇与共享之所。熙笃会的伟大改革者圣伯尔纳铎(克莱尔沃的,San Bernardo de Claraval),「坚决主张度一种俭朴而有节的生活,无论在饮食、服饰或隐修院建筑上,并力劝供养与关怀贫困者。」[45] 对他而言,慈悲绝非可有可无的附加品,而是追随基督的真正途径。因此,当隐修生活忠于其原始圣召时,它便昭示:教会唯有同时成为贫困者的姊妹,才能全然成为主的净配。回廊绝非遁世之避所,而是学习如何更好地服务世界之学堂。在隐修士们为贫困者敞开大门之处,教会便以谦抑而坚定的姿态启示:默观绝不排斥慈悲,反而要求慈悲作为其最纯净的果实。
解救被掳者
59.自宗徒时代起,教会便在解救受压迫者的行动中,视其为天主之国的标记。耶稣在开始其公开使命时,便亲自宣告:「上主的神临於我身上,因为祂给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被掳的人宣告释放」(路4:18)。即使在艰困的处境中,早期的基督徒仍如《宗徒大事录》(参12:5;24:23)及众多教父著作所见证的那样,祈祷并援助被囚的弟兄姐妹。这项解救的使命在数个世纪中,藉着具体的行动得以延续,尤其是在奴役与囚虏的悲剧笼罩整个社会的时期。
60.在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当地中海区域有许多基督徒被俘,或在战争中被奴役时,兴起了两个修会:由圣若望·玛达(San Juan de Mata) 和圣斐理斯·德·瓦洛伊斯(San Félix de Valois) 创立的 「至圣圣三与俘虏赎主会」(Orden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Redención de Cautivos) ,以及由圣伯多禄·诺拉斯科(San Pedro Nolasco) 在道明会士圣赖孟多·佩尼亚福特(San Raimundo de Peñafort) 的支持下创立的 「圣母仁慈之母会」(Orden de la Bienaventurada Virgen María de la Merced) 。这些献身团体诞生的特定神恩,便是解救被奴役的基督徒,他们不仅倾其财物,[46] 更常常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圣三会士(Trinitarios) 以「愿光荣归于祢、圣三,愿自由归于俘虏」(Gloria Tibi Trinitas et captivis libertas)为格言;而仁慈会士(Mercedarios) 则在神贫、贞洁、服从三愿之外,附加了第四愿,[47] 即甘愿为解救信友而被扣留。他们共同见证了爱德可以达至英雄的境界。解救俘虏是圣三之爱的表达:这位解救人的天主,不仅使人摆脱神性的奴役,也使人脱离具体的压迫。从奴役和监禁中赎救的行为,被视为基督救赎性牺牲的延续,祂的宝血便是我们赎价的代价(参格前6:20)。
61.这些修会独特的灵修,深深植根于对十字架的默观。基督是俘虏的赎身者的卓越典范,而教会,作为祂的身体,便在时间中延续这项奥迹。[48] 会士们视赎房之举,非为政治或经济行为,而近乎一项礼仪行动,一种圣事性的自我奉献。许多人献出自己的身体去替代被囚者, 一字不差地践行了「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若15:13)这诫命。这些修会的传统从未中断。相反,它激励了面对现代奴役形态的新行动:人口贩卖、强迫劳动、性剥削、各种成瘾。[49] 基督徒的爱德一旦具体化,便成为解救性的。而教会的使命,当它忠于其主时,便永远是宣告解放。即便在今天,仍有「数百万计的人——包括儿童、男人、各年龄层的女性——被剥夺自由,被迫生活在类似奴隶的境况中」,[50] 这份遗产正由这些修会以及其他在都市边缘、冲突地区、移民走廊服务的机构与修会所承继。当教会屈膝去折断束缚贫困者的新锁链时,她便成了逾越奥迹的标记。
62.在结束关于被剥夺自由者的省思时,不能不提及身处各类看守所与监狱中的囚犯。关于此点,当忆及教宗方济各对他们中的一群人所讲的话:「对我来说,进入监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监狱是一个充满人性尊严的场所……这是经受考验的人性,有时因困难、罪恶感、审判、误解、痛苦而疲惫,但同时又充满了力量、对宽恕的渴望、对救赎的渴望。」[51] 这份渴望,连同其他,亦被赎虏修会视为对教会的优先服务而接纳。正如圣保禄所宣告的:「基督解救了我們,是為使我們獲得自由」(迦5:1)。而这自由不仅是内在的:它在历史中彰显为那看顾人、并从一切束缚中解救出来的爱。
福音神贫的见证
63.十三世纪时,面对城市的兴起、财富的集中及新形态贫困的出现,圣神在教会内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献身生活:托钵修会。不同于稳定的隐修模式,托钵会士们度一种巡游的生活,无个人亦无团体的恒产,完全仰赖上智的眷顾。他们不仅服务穷人,更与穷人同贫。他们将城市视为新的旷野,将边缘者视为新的灵修导师。这些修会,如方济各会、道明会、奥斯定会和加尔默罗会,代表了一场福音革新,其中简朴与贫穷的生活方式成为福传的先知性标记,重现了早期基督徒团体的经验(参宗4:32)。托钵会士的见证,既挑战了圣职界的豪奢,也叩问了城市社会的冷漠。
64.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成为这灵性春天的典范。他以贫穷为净配,愿效法那位贫穷、赤身、被钉的基督。在其《会规》中,他要求弟兄们「不占有任何事物,无论房屋、地方,或其他任何物品。在此世度着朝圣者与异乡人的生活,在贫穷与谦卑中服事上主,当安心行乞,不应感到羞耻,因为上主在此世为我们成了贫穷的。」[52] 他的生命是一场持续的自我空虛:从宫殿到癞病人身旁,从雄辩到静默,从占有到全然的赠与。方济各创立的并非一项社会服务,而是一个福音性的兄弟会。在穷人身上,他看见弟兄,看见主的活肖像。他的使命是与他们同在,藉着一种超越距离的共融,藉着一种慈悲的爱。他的贫穷是关系性的:这贫穷引领他成为亲近者、平等者,甚或更微末者。他的圣德源于一个信念:唯有在向弟兄慷慨地奉献自我时,才能真正接纳基督。
65.亚西西的圣佳兰受方济各启发,创立了贫穷淑女会,即后来的佳兰会。她的灵性奋斗在于忠信持守彻底神贫的理想。她拒绝了可能保障其隐修院物质安全的宗座特权,并以坚定之心,从教宗额我略九世那里获得了所谓的 「贫穷特权」 ,此特权保障了她们 「不拥有任何物质财产」而生活的权利。[53] 此抉择表达了对天主全然的信赖,并明认自愿的贫穷乃是一种自由与先知性的行动。佳兰教导她的姊妹们:基督是她们唯一的产业,任何事物都不可模糊与祂的共融。她那祈祷与隐藏的生活,是对世俗精神的一声呐喊,也是对贫困者与被遗忘者无声的捍卫。
66.与方济各同时代的圣道明·古斯曼,以另一种神恩但同样的彻底精神创立了宣道会。他渴望以源于贫穷生活的权威宣讲福音,深信真理需要言行一致的见证人。生活的贫穷榜样伴随着所宣讲的圣言。从世间财物的重担中解脱出来,道明会会士们能更专务于首要工作,即宣讲。他们前往城市,尤其是那些大学城,去教导天主的真理。[54] 藉着依赖他人,他们表明信仰并非强加于人,而是奉献于人。并且,藉着生活在穷人中间,他们「从底层」学习福音的真理,如同受屈辱之基督的门徒。
67.如此,托钵修会便成了对排斥与冷漠的一个鲜活回应。他们并未明确提议社会改革,而是呼吁个人与团体的皈依,归向天国的逻辑。在他们身上,贫穷并非财物匮乏的后果,而是一项自由的抉择:成为微末的,为接纳微末者。正如策肋的多玛斯论及方济各时所言:「在他身上显现为贫穷者的首爱者……他脱下自己的衣裳,以此衣蔽穷人,他设法——即使尚未完全在事实上,却已在全心渴望中——与他们相似。」[55] 托钵会士们已成为一个旅世的、谦卑的、兄弟般的教会的标记,她生活在穷人中间,非因劝诱改宗的策略,而是出于身份本质。他们教导:教会唯有舍弃一切才能成为光明,而圣德必经由一颗谦卑并倾注于微末者之心。
教会与穷人的教育
68.教宗方济各曾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说,教育始终是基督徒爱德的崇高表现之一:“你们的使命虽然充满困难,但也充满喜乐......这是一个爱的使命,因为没有爱就无法教导。”[56] 从这个角度看,基督徒从早期就认识到知识能使人得自由、有尊严、近真理。对教会来说,教育穷人是一种正义和信德的行动。效法那位教导人们神圣与人间真理的导师,教会承担起了在真理和爱中培育儿童和青年,特别是最贫困者的使命。随着专门从事平民教育的修会成立,这一使命得以具体化。
69.十六世纪,圣若瑟·卡拉桑斯(San José de Calasanz)看到罗马城里贫困青年缺乏教育和培养的状况,深受触动。他在特拉斯特维雷的圣多罗特亚教堂旁的几间屋子里,创办了欧洲第一所免费的公立平民学校。这是一颗种子,后来虽经历困难,但最终发展成了“天主之母贫穷正则学校神职修会”,会士被称为“卡拉桑斯会士”。该修会的宗旨是向青年传授“世俗知识和福音的智慧,教导他们在个人经历和历史中发现天主作为创造者和救赎者的慈爱行动。”[57]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这位勇敢的神父视为“现代天主教学校的真正奠基人——这类学校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并向所有人开放。”[58] 怀着同样的情怀,十七世纪的圣若望·喇沙(San Juan Bautista de La Salle)意识到当时法国教育体系将工人和农民子女排除在外所造成的不公,创立了“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理想是为这些孩子提供免费教育、扎实的培养和兄弟般的氛围。喇沙把课堂看作既是发展人性的地方,也是悔改的地方。他的学校将祈祷、方法、纪律和分享结合在一起。每个孩子都被视为天主独特的恩赐,而教学行为本身就是对天主的国服务。
70.到了十九世纪,同样在法国,圣马塞利诺·尚帕尼亚(San Marcelino Champagnat)创立了“圣母昆仲会”。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灵性和教育需求,特别是青年人所处的宗教无知和被遗弃的境况”[59],在一个受教育机会仍是少数人特权的时代,他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和福传儿童及青年,尤其是最有需要者的使命中。本着同样的精神,在都灵,圣若望·鲍思高(San Juan Bosco)开创了撒肋爵会的事业,其基础是“预防教育法”的三个原则——理性、宗教、仁爱[60];真福安东尼奥·罗斯米尼(Beato Antonio Rosmini)则创立了“仁爱会”,在该会中,“理智的爱德”——与“物质的爱德”并列,且位于顶端的是“灵修-牧灵的爱德”——被呈现为任何着眼于“人的福祉和全面发展”的爱德行动所不可或缺的维度。[61]
71.许多女修会也是这场教育革新的主角。圣乌尔苏拉会、圣母修女会、虔敬女修会以及许多其他尤其在十八、十九世纪创立的修会,填补了政府缺席的领域。她们在小村庄、郊区和工人街区创建学校。女童教育尤其成为一项优先任务。修女们教穷人识字、进行福传、处理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通过培养艺术来提升心灵,并且最重要的是塑造良知。她们的教育方法简单而真诚:亲近、耐心、温柔。她们以身教重于言教。在普遍文盲和存在结构性排斥的时代,这些献身女性是希望的灯塔。她们的使命是塑造心灵、教导思考、促进尊严。她们将虔敬的生活和对近人的奉献结合起来,以奉基督之名的温柔来对抗被遗弃的状况。
72.对基督徒的信仰而言,教育穷人不是恩惠,而是责任。弱小者有权获得智慧,这是承认人性尊严的基本要求。教育他们是肯定他们的价值,是给予他们改变自身现实的工具。基督徒传统认为,知识是天主的恩赐,也是团体的责任。基督徒教育培养的不仅是专业人士,更是向善、向美、向真理开放的人。因此,当天主教学校忠于其名时,它就成为一个包容、全面培养和促进人性的空间。这样,信仰与文化相结合,播种未来,尊崇天主的肖像,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陪伴移民
73.移民的经历伴随着天主子民的历史:亚巴郎启程时不知往哪里去;梅瑟带领朝圣的子民穿越沙漠;玛利亚和若瑟带着婴孩逃往埃及。就连“祂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祂”(若望福音 1:11)的基督,也曾在我們中间作为异乡人生活。因此,教会始终在移民身上认出主活生生的临在,在审判之日,祂将对右边的人说:“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玛窦福音 25:35)
74.十九世纪,当数百万欧洲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移民时,有两位伟大的圣人在关怀移民的牧灵工作中脱颖而出:圣若望·鲍思高·斯卡拉布里尼(San Juan Bautista Scalabrini)和圣方济加·沙勿略·卡布里尼(Santa Francisca Javier Cabrini)。时任皮亚琴察主教的斯卡拉布里尼创立了圣嘉禄传教会,陪伴移民到达目的地团体,为他们提供灵性、法律和物质援助。他在移民身上看到了新福传的对象,并警惕他们在异国他乡遭受剥削和丧失信仰的风险。他慷慨地回应天主赐予的神恩,“斯卡拉布里尼看得更远,展望未来——一个没有隔阂、没有外人的世界与教会。”[62] 圣方济加·卡布里尼生于意大利,后加入美国籍,成为首位被册封为圣人的美国公民。为了完成关怀移民的使命,她多次横渡大西洋,“凭着非凡的勇气,白手起家,为无数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建造学校、医院和孤儿院——这些人冒险到新世界寻找工作,却不谙语言、缺乏资源,无法有尊严地融入北美社会,还常常成为无耻之徒的受害者。她那颗永不气馁的慈母之心,无论他们在何处——贫民窟、监狱还是矿山——都能找到并亲近他们。”[63] 在1950年的圣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她为所有移民的主保。[64]
75.教会与移民同行、为移民服务的传统延续至今,如今这项服务体现在诸如难民接待中心、边境传教站,以及国际明爱会和其他机构的努力中。当代教会训导也明确重申这一承诺。教宗方济各曾提醒,教会陪伴移民和难民的使命更为广泛,他强调“应对当代移民挑战的答案可以概括为四个动词:接纳、保护、促进、融合。但这四个动词不仅适用于移民和难民。它们表达了教会对于所有身处生存边缘者的使命——他们都应被接纳、保护、促进与融合。”[65] 他补充道:“每个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在他们身上印有基督的肖像。因此,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看到这肖像,进而能帮助他人认识到,在移民和难民身上,我们不应只看到‘需要应对的问题’,而应看到‘需要被接纳、尊重和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天主的眷顾提供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借此为建设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更成熟的民主、更团结的国家、更友爱的世界,以及一个更开放、符合福音精神的基督徒团体贡献力量。”[66] 教会如同母亲,与行路者同行。在世人看到威胁的地方,她看到子女;在人们筑起高墙的地方,她搭建桥梁。她知道,福音的宣报只有转化为亲近与接纳的行动时才可信;她也知道,在每一个被拒绝的移民身上,正是基督本人在叩响团体的大门。
与最卑微者同在
76.基督徒的圣德常常在人类最被遗忘、最受创伤的地方绽放。穷人中的至贫者——那些不仅缺乏物质,也失去声音、其尊严不被承认的人——在天主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是福音中的优先者,是天国的继承者(参看路加福音 6:20)。基督正是在他们身上继续受苦并复活。教会也正是在他们身上,重新发现那召唤她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使命。
77.圣德兰修女(Santa Teresa de Calcuta)于2016年被册封为圣人,成为为被社会遗弃的赤贫者活出极致爱德的普世象征。作为仁爱传教女修会的创始人,她将一生奉献给在印度街头被遗弃的临终者:她收容被拒绝的人,清洗他们的伤口,并以一种如同祈祷的温柔陪伴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对“穷人中的至贫者”的爱,不仅驱使她去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也促使她向他们宣报福音的喜讯:“我们愿向穷人传报喜讯:天主爱他们,我们爱他们,他们对我们至关重要,他们同样是由那慈爱的天主亲手所造,为去爱与被爱。我们的穷人是伟大的人,是非常可爱的人,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怜悯与同情,他们需要的是我们带有理解的爱、尊重,以及有尊严的对待。”[67] 这一切源于一种深邃的灵修,她将服务至贫者视为祈祷与爱的果实,而这爱能带来真正的平安。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向前往罗马参加其真福品典礼的朝圣者所回忆的:“德兰修女从何处获得这完全为他人服务的力量?她是从祈祷和对耶稣基督、祂的圣容和圣心的静默默观中获得的。她亲口说过:‘静默的果实是祈祷;祈祷的果实是信德;信德的果实是爱;爱的果实是服务;服务的果实是平安。’……祈祷使她的心充满基督的平安,并使她能将这平安放射给他人。”[68] 德兰从不自视为慈善家或社会活动家,而是被钉十字架基督的净配——她在受苦的弟兄身上,以全然的爱去服事祂。
78.在巴西,圣杜尔丝·德洛斯·波夫雷斯(Santa Dulce de los Pobres),被称为“巴伊亚的善良天使”,以巴西的特色活出了同样的福音精神。在提及她与同期被册封为圣人的另外两位修女时,教宗方济各回顾了她们对社会最边缘者的爱,并肯定这些新圣人们“向我们表明,献身生活是在世界生存边缘活出爱的道路。”[69] 杜尔丝修女以创造力面对匮乏,以温柔克服障碍,以坚不可摧的信德应对短缺。她从在一个鸡舍里收容病人开始,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该国最大的社会事业之一。她每天服务数千人,却从未失去她的温柔。她为了爱那“至贫穷者(指基督)”,而与穷人同贫。她生活简朴,祈祷热切,服务喜乐。她的信德并未使她远离世界,反而让她更深入地沉浸于最卑微者的痛苦之中。
79.我们还应忆起:服务残疾人的圣本笃·门尼(San Benito Menni)和耶稣圣心医院修女会;在撒哈拉团体中生活的圣夏尔·德·富科(San Carlos de Foucauld);服务北美最弱势群体的圣凯瑟琳·德雷克塞尔(Santa Katharine Drexel);在开罗埃兹贝特·纳赫尔区与拾荒者同行的艾曼纽修女(Hermana Emmanuelle);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各自发现,至贫者并非仅仅是怜悯的对象,更是福音的导师。问题不在于“把天主带给他们”,而在于“在他们中间遇见天主”。所有这些榜样都教导我们,服务穷人并非一种自上而下的举动,而是平等者之间的相遇——在此相遇中,基督彰显自己并受人钦崇。圣若望·保禄二世曾提醒我们:“在穷人身上,有基督的一种特殊临在,这要求教会作出对他们的优先选择。”[70] 因此,当教会俯身至地去关怀穷人时,便活出了她最崇高的姿态。
民众运动
80.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整个基督徒历史中,对穷人的援助和为他们的权利而奋斗,并不仅仅涉及个人、某些家庭、机构或宗教团体。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民众运动,由平信徒组成,由民众领袖领导,这些领袖常常受到猜疑甚至迫害。我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属于众人、为了众人’的团体网络前行,不能让最贫穷和最弱小者掉队。……因此,民众领袖就是那些有能力‘接纳所有人’的人。……他们对‘受伤和被钉的青年’既不厌恶,也不惧怕。”[71]
81.这些民众领袖深知,团结“也意味着与贫困、不平等、缺乏工作、土地和住房、社会与劳工权利被剥夺的结构性原因作斗争;是面对金钱帝国的破坏性影响……。从最深层的意义理解,团结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式,而民众运动正是在这样做。”[72] 因此,当各种机构考虑穷人的需求时,需要“将民众运动纳入其中,并以这股源于让被排斥者参与共同命运构建而迸发出的道德力量,去激励地方、国家和国际的治理结构。”[73] 事实上,民众运动邀请我们超越“那种将社会政策视为‘针对穷人’的政策,却从来不是‘与穷人一起’、‘源于穷人’的政策,更不是融入一个‘团结民族’计划的想法。”[74] 如果政治家和专业人士不倾听他们的声音,“民主就会萎缩,变成名义上的、形式化的东西,失去代表性,逐渐脱离肉身,因为它将人民——在他们为尊严进行的日常奋斗中,在他们构建自身命运的过程中——排除在外。”[75] 对于教会的机构,同样可以如此断言。
参考文献
[19] 方济各,与媒体代表会晤(2013年3月16日):《宗座公报》105(2013),381页。
[20]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万民之光》教义宪章,8号。
[21] 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48号:《宗座公报》105(2013),1040页。
[22] 在本章中,我们将提出这些圣德的例子,它们并非旨在穷尽,而是指示教会临在于世始终具有的对穷人的关怀。关于教会对最贫困者关怀历史的详细反思,见于 V. Paglia, Storia della povertà, 米兰 2014。
[23] 参圣安博,《论圣职人员的职责》卷一,41章,205-206节:CCSL 15, Turnhout 2000, 76-77页;卷二,28章,140-143节:CCSL 15, 148-149页。
[24] 同上,卷二,28章,140节:CCSL 15, 148页。
[25] 同上。
[26] 同上,卷二,28章,142节:CCSL 15, 148页。
[27] 圣依纳爵·安提约基亚,《致斯米纳书》,6, 2:SCh 10bis, 巴黎 2007, 136-138页。
[28] 圣波利卡普,《致斐理伯人书》,6, 1:SCh 10bis, 186页。
[29] 圣犹斯定,《第一护教辞》,67, 6-7:SCh 507, 巴黎 2006, 310页。
[30] 圣金口若望,《玛窦福音讲道集》,50, 3:PG 58, 巴黎 1862, 508栏。
[31] 同上,50, 4:PG 58, 509栏。
[32] 同一位教父,《致希伯来人书讲道集》,11, 3:PG 63, 巴黎 1862, 94栏。
[33] 同一位教父,《论拉匝禄讲道第二篇》,6:PG 48, 巴黎 1862, 992栏。
[34] 圣安博,《论纳布特》,12, 53:CSEL 32/2, 布拉格-维也纳-莱比锡 1897, 498页。
[35] 圣奥思定,《圣咏释义》,125, 12:CSEL 95/3, 维也纳 2001, 181页。
[36] 同一位教父,《讲道集第八十六篇》,5:CCSL 41Ab, Turnhout 2019, 411-412页。
[37] 伪奥思定,《讲道集第三百八十八篇》,2:PL 39, 巴黎 1862, 1700栏。
[38] 圣西彼廉,《论死亡》,16:CCSL 3A, Turnhout 1976, 25页。
[39] 方济各,第三十届世界病人日文告(2021年12月10日),3号:《宗座公报》114(2022),51页。
[40] 圣嘉民·雷利斯,《病人之仆协会会规》,27条:M. Vanti (编), Scritti di San Camillo de Lellis, 米兰 1965, 67页。
[41] 圣路易丝·玛利亚克,致克劳德·卡雷修女和玛丽·高杜安修女的信(1657年11月28日):E. Charpy (编), Sainte Louise de Marillac. Écrits, 巴黎 1983, 576页。
[42] 圣大巴西略,《详规》,37, 1:PG 31, 巴黎 1857, 1009 C-D栏。
[43] 《本笃会规》,53, 15:SCh 182, 巴黎 1972, 614页。
[44] 圣若望·卡西安,《会谈录第十四篇》,10:CSEL 13, 维也纳 2004, 410页。
[45] 本笃十六世,要理讲授(2009年10月21日):《罗马观察报》,西班牙文周刊版,2009年10月23日,32页。
[46] 参依诺增爵三世,《神圣安排运作》诏书——圣三会原始会规(1198年12月17日),2号:J. L. Aurrecoechea – A. Moldón (编), Fuentes históricas de la Orden Trinitaria (s. XII-XV), 科尔多瓦 2003, 6-7页:「所有财物,无论来自何处,只要是合法所得,皆应平分为三份;只要其中两份足够,就用它们施行慈善工作,并维持自身及因需要而服务者适度的生计。相反,第三份应保留用于赎救那些因对基督的信仰而被囚的俘虏」。
[47] 参圣母仁慈会会宪,14号:圣母仁慈圣母玛利亚会,《会规与会宪》,罗马 2014, 53页:「为完成此使命,在爱德推动下,我们藉一种称为'赎救'的特愿奉献于天主,藉此我们许诺,如有必要,为拯救那些在新的奴役形式下信仰处于极度危险中的基督徒,献出生命,如同基督为我们献出生命一样」。
[48] 参圣若翰·佘也,《圣三会会规》,XX, 1:BAC Maior 60, 马德里 1999, 90页:「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俘虏与基督相似,世界将痛苦倾倒在基督身上……。这个至圣圣三的圣修会召唤并邀请他们来饮救主的水,这就是说,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人类的救恩和救主,祂已取得那救恩,并愿意给予并分施给穷人,拯救并解救俘虏」。
[49] 参同一位圣者,《内心的收敛》,XL, 4:BAC Maior 48, 马德里 1995, 689页:「自由意志使人成为所有受造物中的主人和自由者,但是,唉,我的天主!有多少人因此反而成了魔鬼的奴隶和俘虏,被自己的私欲偏情所囚禁和束缚」。
[50] 方济各,第四十八届世界和平日文告(2014年12月8日),3号:《宗座公报》107(2015),69页。
[51] 同一位教宗,在蒙托里奥(维罗纳)监狱与狱警、囚犯和义工会晤(2024年5月18日):《宗座公报》116(2024),766页。
[52] 何诺理三世,《惯常批准》诏书——获准会规(1223年11月29日),第六章:SCh 285, 巴黎 1981, 192页。
[53] 参额我略九世,《显而易见》诏书(1228年9月17日),7号:SCh 325, 巴黎 1985, 200页:「因此,正如你们所恳求的,我们以宗座的恩宠加强你们追求至高贫穷的决心,藉本诏书的权威授予你们特权,使你们不能被强迫接受任何人的财产」。
[54] 参 S. C. Tugwell (编), Early Dominicans. Selected Writings, Mahwah 1982, 16-19页。
[55] 托马索·达·切拉诺,《第二生平——第一部分》,第四章,8节:AnalFranc 10, 佛罗伦萨 1941, 135页。
[56] 方济各,访问洛伦佐·米拉尼神父墓后讲话(巴尔比亚纳,2017年6月20日),2号:《宗座公报》109(2017),745页。
[57] 圣若望保禄二世,向圣母献主会——慈幼会总会议参与者讲话(1997年7月5日),2号:《罗马观察报》,西班牙文周刊版,1997年7月11日,2页。
[58] 同上。
[59] 同一位教宗,封圣弥撒讲道(1999年4月18日):《宗座公报》91(1999),930页。
[60] 参同一位教宗,《青年之父》宗座书信(1988年1月31日),9号:《宗座公报》80(1988),976页。
[61] 参方济各,向仁爱会——罗西米尼会总会议参与者讲话(2018年10月1日):《罗马观察报》,2018年10月1-2日,7页。
[62] 同一位教宗,封圣弥撒讲道(2022年10月9日):《宗座公报》114(2022),1338页。
[63] 圣若望保禄二世,致圣心传教女修会文告(2000年5月31日),3号:《罗马观察报》,西班牙文周刊版,2000年7月28日,5页。
[64] 参庇护十二世,《年事已高》宗座简短(1950年9月8日):《宗座公报》43(1951),455-456页。
[65] 方济各,第一零五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2019年5月27日):《宗座公报》111(2019),911页。
[66] 同一位教宗,第一零零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2013年8月5日):《宗座公报》105(2013),930页。
[67] 圣德肋撒姆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辞(奥斯陆,1979年12月10日):同一位,《爱至成伤》,里昂 2017, 19-20页。
[68] 圣若望保禄二世,向为德肋撒姆姆列真福品前来罗马的朝圣者讲话(2003年10月20日),3号:《罗马观察报》,西班牙文周刊版,2003年10月31日,7页。
[69] 方济各,封圣弥撒讲道(2019年10月13日):《宗座公报》111(2019),1712页。
[70] 圣若望保禄二世,《新千年的开始》宗座书信(2001年1月6日),49号:《宗座公报》93(2001),302页。
[71] 方济各,《生活的基督》宗座劝谕(2019年3月25日),231号:《宗座公报》111(2019),458页。
[72] 同一位教宗,向世界平民运动参与者讲话(2014年10月28日):《宗座公报》106(2014),851-852页。
[73] 同上:《宗座公报》106(2014),859页。
[74] 同一位教宗,向世界平民运动参与者讲话(2016年11月5日):《罗马观察报》,西班牙文周刊版,2016年11月11日,8页。
[7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