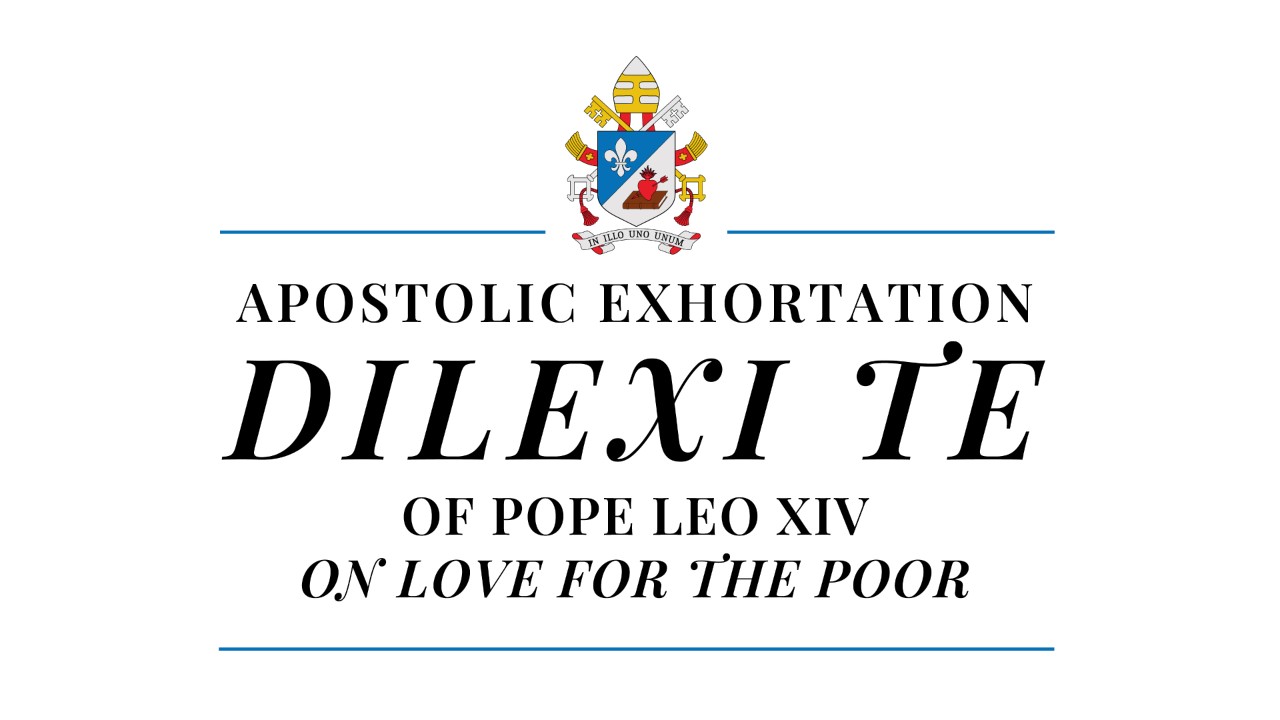《我爱了你》宗座劝谕 连载 第四章
发布日期:2025-10-16 | 作者:大海翻译《我爱了你》(Dilexi Te)
论对贫困者的爱
——教宗良十四世——
第四章 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
教会社会训导的世纪
82.近两个世纪以来,技术与社会变革加速推进,其间充满悲剧性矛盾。面对这一切,穷人不仅承受苦难,更主动应对、深入思考。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以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让“边缘者的尊严”逐渐形成新的共识。教会社会训导的成果,也深深植根于这一不可遗忘的民众根基;若没有基督徒平信徒直面时代挑战,便无法想象教会能在现代社会、劳动、经济与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基督的启示。与平信徒并肩行动的,还有修女和修士们(religiosas y religiosos)——他们是教会“走出固有路径、迈向新领域”的见证者。如今我们面临的时代变革,更迫切需要“已受洗者与教会训导、公民与专家、民众与机构”之间的持续互动。尤其需要重申的是:从边缘地带更能看清现实真相,穷人拥有“独特的智慧”——这对教会与人类而言不可或缺。
83.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教会训导,为“关怀穷人”提供了丰富的教导资源。罗马主教们(Obispos de Roma,即教宗)成为“新共识的发声者”,这些共识也被纳入教会的分辨过程。例如,良十三世(León XIII)在1891年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中,直面劳动问题:揭露工业时代许多工人难以忍受的处境,并倡导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后续教宗也沿此方向发声:圣若望二十三世(san Juan XXIII)在1961年的《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通谕中,推动“具有全球维度的正义”——富裕国家不应对“受饥饿与苦难压迫的国家”无动于衷,而应慷慨地倾其所有资源援助他们。
84.从启示的光照下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教会“分辨穷人议题”的关键阶段。尽管在预备文件中,这一主题曾处于边缘,但1962年9月11日(距大公会议开幕仅一个月),圣若望二十三世在广播讲话中,以令人难忘的话语将焦点汇聚于此:“教会呈现其本真面貌,也呈现其渴望成为的模样——它是所有人的教会,尤其应是穷人的教会。”[76] 正是在圣若望二十三世本人的支持下,“关注教会革新的主教、神学家与专家们”共同努力,为大公会议重新定向。这场革新的核心,在于其“以基督为中心”(cristocéntrica)的本质——即具有教义维度,而非单纯的社会运动。事实上,众多与会教长们推动了这一共识的巩固,正如莱卡洛枢机(cardenal Lercaro)在1962年12月6日的难忘发言中所言:“基督在教会中的奥迹,始终——尤其在今日——是基督在穷人中的奥迹”[77],且“这并非新增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梵二大公会议唯一的核心议题”[78]。这位博洛尼亚总主教(arzobispo de Bolonia)在准备发言稿时曾写道:“此刻是穷人的时刻——是遍布全球数百万穷人的时刻;此刻是教会作为‘穷人之母’的奥迹的时刻;此刻是基督尤其在穷人中彰显其奥迹的时刻。”[79] 由此,一种“更简朴、更节制的教会新形态”的需求逐渐清晰——它需涵盖全体天主子民及其在历史中的形象,应更相似于其主、而非世俗权柄,旨在激励全人类采取具体行动,解决世界贫困这一重大问题。
85.圣保禄六世(san Pablo VI)在大公会议第二届会议开幕时,延续了其前任提出的主题,指出教会“尤其关注穷人、有需要者、受苦者、饥饿者、病人、囚犯——即所有受苦哭泣的人类;他们凭福音的权利,属于教会”[80]。在1964年11月11日的周三公开接见中,他进一步强调“穷人是基督的代表”,并将“主在最卑微者身上的临在”与“主在教宗身上的临在”相联系,断言:“基督在穷人中的代表身份是普世的——每一个穷人都反映基督;而基督在教宗身上的代表身份是个人性的…… 穷人与伯多禄(Pedro,指教宗)的身份可以合一:同一个人可同时承载两种代表身份——贫困的代表与权威的代表。”[81] 如此,教会与穷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独特而清晰的象征方式得以表达。
86.梵二大公会议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即《喜乐与期望》)中,继承教会教父们的遗产,明确肯定“大地财物的普遍归宿”,以及由此衍生的“财产的社会功能”:“天主将大地及其一切物产,定为全人类及各民族共用之物。因此,受造物应惠及所有人…… 人在使用外在财物时,不应将自己合法拥有的物品视为专属己有,而应视为‘共有之物’——即不仅为自身益处,也为他人福祉。此外,‘拥有足够财物以供养自身及家庭’,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 处于极端困境者,有权从他人的财富中获取自身所需…… 私有财产就其本质而言,也具有社会性——其根基在于‘财物的共同归宿’。若忽视这一社会性,财产往往会成为‘野心的工具’,引发严重的混乱。”[82] 圣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中,再次强化这一信念:我们读到,任何人都无权“将超出自身需求的财物据为己有,而置他人的需求于不顾”[83]。在联合国的演讲中,蒙蒂尼教宗(Papa Montini,即圣保禄六世)以“贫穷民族的辩护人”身份[84],呼吁国际社会构建一个团结的世界。
87.在圣若望·保禄二世(san Juan Pablo II)的训导中,至少在教义层面,教会与穷人的“优先关系”得以巩固。事实上,他的教导承认,“优先选择穷人”是“基督徒爱德实践的特殊核心——教会的整个传统都为此作证”[85]。他在《社会事务关怀》(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谕中还写道:如今,社会问题已具备全球维度,“这份优先之爱,及其所启发的抉择,必然涵盖无数‘饥饿者、乞丐、无家可归者、缺乏医疗照料者,尤其失去未来希望者’;我们无法忽视这一现实。忽视它,便会沦为‘富有的饕餮者’——正如那个对门前的乞丐拉匝禄视而不见的人(参见《路加福音》16:19-31)”[86]。当我们思考“穷人在教会与社会革新中的积极作用”,并摒弃“仅提供即时援助的家长式作风”时,他关于“工作”的教导便显得尤为重要。在《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通谕中,他断言:“人之工作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或许是核心关键。”[87]
88.面对第三个千年之初的多重危机,本笃十六世的解读更具鲜明的政治维度。他在《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谕中指出:“我们对近人的爱越有效,就越需为‘满足其真实需求的共同善(bien común)’而努力。”[88] 此外,他观察到:“饥饿问题的根源,更多在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性资源,而非物质短缺。也就是说,我们缺乏这样的经济机构体系:它既能确保人们‘定期获得营养充足的水与食物’,又能应对‘基本需求相关的要求’及‘由自然灾害或国家与国际层面政治失职引发的实际粮食危机’。”[89]
89.教宗方济各承认,除历任罗马主教的训导外,近几十年来,各国及地区主教团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也日益频繁。例如,他曾亲身见证拉丁美洲主教团在“反思教会与穷人关系”上的特殊投入。在后大公会议时期,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强烈感受到“教会与穷人的认同”,以及教会“积极参与解救穷人”的行动。面对无数穷人承受失业、半失业、不公薪资,被迫生活在悲惨处境中的景象,教会的心灵被深深触动。圣萨尔瓦多总主教圣奥斯卡·罗梅罗(san Óscar Romero)的殉道,既是教会的见证,也是鲜活的劝勉——他将绝大多数信众的苦难视为己任,并将其作为自己牧灵抉择的核心。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麦德林(Medellín)、普埃布拉(Puebla)、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与阿帕雷西达(Aparecida)召开的会议,也成为整个教会的重要里程碑。我本人曾在秘鲁担任传教士多年,深深受益于这条教会分辨之路——教宗方济各巧妙地将其与其他地方教会(尤其全球南方教会)的分辨之路相联结。此刻,我想谈谈主教训导中两个具体议题。
导致贫困与极端不平等的罪恶结构
90.在麦德林会议(Conferencia de Medellín)中,主教们明确支持“优先选择穷人”的立场:“我们的救主基督,不仅爱了穷人,更‘祂虽是富有的,却为了你们成了贫困的’,在贫穷中生活,将其使命核心放在‘向穷人宣告他们的解放’上,并建立祂的教会,作为在人间彰显这一贫穷的记号。……无数弟兄的贫困,呼唤正义、团结、见证、奉献、努力与超越,以圆满实现基督托付的救赎使命。”[90] 主教们坚定主张:教会若要全然忠实于自身召叫,不仅需认同穷人的处境,更需站在他们一边,勤勉地投入促进他们整体发展的工作。面对拉丁美洲贫困加剧的现状,普埃布拉会议(Conferencia de Puebla)以“坦诚且具先知性的优先选择穷人”之决定,确认了麦德林会议的决议,并将不义的结构界定为 “社会性罪恶”(pecado social)。
91.爱德是“改变现实的力量”,是“推动历史变革的真实力量”。它是所有“解决贫困结构性原因”[91] 的行动都应参照的源头,且这一行动刻不容缓。因此,我祈求“有更多政治家能开展真正的对话,切实致力于医治我们世界弊病的深层根源,而非仅处理表面问题”[92]——因为“这关乎聆听整个民族的呼声,关乎全球最贫困民族的呼声”[93]。
92.因此,我们必须持续疾呼“致死经济的独裁”,并认清:“当少数人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时,大多数人的福祉与这一幸运少数群体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这种失衡源于‘捍卫市场绝对自主与金融投机)’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类意识形态否定了‘国家的监管权’,而国家本应承担‘维护共同善’的职责。一种新的隐形独裁(有时是虚拟的,virtual)就此形成,它单方面、无情地强加自己的法则与规则。”[94] 尽管不乏各类理论试图为现状辩护,或声称“经济理性要求我们等待市场无形力量自行解决一切”,但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必须“此刻便得到尊重,而非等到明天”;那些“尊严被剥夺、深陷悲惨处境的人们”,其遭遇必须持续叩击我们的良知。
93.教宗方济各在《祂爱我们》(Dilexit nos)通谕中回顾道,社会性罪恶(pecado social) 在社会中会呈现 "罪恶结构"的形态,这种结构"往往......嵌入一种主流心态中,将无非是自私与冷漠的事物视为正常或合理。这种现象可被定义为'社会异化'"[95]。忽视穷人、仿佛他们不存在般生活已变得稀松平常;"要求民众做出牺牲来组织经济,以实现权势者关心的某些目标"被包装成理性选择;而留给穷人的只有"零星恩惠"的承诺——直到新的全球危机将他们打回原形。真正的异化,是只知为现状寻找理论借口,却不愿在当下解决受苦者面临的具体问题。圣若望·保禄二世早已指出:"一个社会若在其社会组织、生产和消费方式上,使人更难实现这种自我奉献和形成那种人际团结,这样的社会便是异化的。"[96]
94.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致力于解决贫困的结构性原因。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不仅出于取得成果和整顿社会的实际需要,更是为了医治这个使社会变得脆弱、有失尊严的痼疾——否则只会导致新的危机。那些应对某些紧急情况的援助计划,只应被视为临时措施"[97]。缺乏公平 "是社会弊病的根源"[98]。事实上,"人们常常感觉到,人权在现实中并非人人平等"[99]。
95.实际情况是,"在现行'成功至上(exitista)'和'私有化至上(privatista)'的模式中,投资帮助行动迟缓者、弱小者或能力较弱者 在生活中开辟道路,似乎毫无意义"[100]。反复出现的问题始终是:能力较弱者难道不是人吗?弱小者就没有与我们同等的尊严 吗?那些生来机会较少的人,作为人的价值就更低,只配勉强生存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社会的价值,也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要么重新赢得道德和灵性尊严,要么就会坠入污秽的深渊。如果我们不停下来认真对待此事,就会继续——无论公开还是隐蔽地——使"当前的分配模式 合法化:少数人认为自己有权以某种比例消费,而这种比例根本无法普及,因为地球甚至连这种消费产生的废弃物都无法容纳"[101]。
96.在那些无法指望自上而下解决、需要尽快承担起来的结构性议题 中,包括穷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空间、住房和城市问题。我们知道,"那些克服病态的不信任、接纳不同群体,并将这种整合转化为新发展因素的城市,是多么美好!那些即使在建筑设计中也充满连接人与人、促进人际关系、有利于相互认可的空间的城市,是多么美丽!"[102] 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环境退化、当前发展模式和丢弃文化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103]。事实上,"环境和社会恶化特别影响到地球上最弱小的人"[104]。
97.因此,天主子民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以各种方式发出能唤醒良知、谴责不公、勇于担当的声音——即使这可能显得"愚蠢"。不义的结构必须被认清,并以善的力量摧毁:这需要通过心态转变,也需要借助科学技术,通过制定有效政策来推动社会转型。必须永远记住,福音的提议不仅仅是与主建立个人和私密的关系。这提议更为广阔:"它是天主的国 (参路4:43);是爱那位统治世界的天主。当祂能在我们中间统治时,社会生活就将成为所有人共享兄弟情谊、正义、和平与尊严的领域。因此,福传和基督徒经验都倾向于产生社会后果。我们寻求祂的国。"[105]
98.最后,一份起初未获某些人认同的文件,为我们提供了始终适时的反思:"对于那些捍卫'正统信仰'的人,有时会有人指责他们在面对无法容忍的不公正状况和维持这些状况的政治制度时,表现出消极、纵容或有罪的共谋。灵性上的皈依、对天主和近人的深切之爱、对正义与和平的热忱、对穷人和贫穷的福音性理解,这些都是对所有人的要求,尤其是对牧者和负责人的要求。对信仰纯正的关切,必须与另一种关切相结合:通过完整的超性生活 ,提供一份有效的见证 来服务近人,特别是穷人和受压迫者,以此作为回应。"[106]
穷人作为主体
99.对普世教会的道路而言,阿帕雷西达会议(Conferencia de Aparecida)的分辨成果代表着一项根本恩赐。拉丁美洲主教们在会上阐明,教会对穷人的优先选择 "隐含在基督论的信仰中:即相信那位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使我们因祂的贫穷而富足的天主"[107]。文件将使命置于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情境中,连同其新的、剧烈的失衡 [108],主教们在最终文告中写道:"富人与穷人之间严峻的差异,促使我们更努力地成为懂得分享生命之桌的门徒——这张桌子属于天父所有的儿女,是开放、包容、不让任何人缺席的桌子。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对穷人福音性的优先选择。"[109]
100.与此同时,该文件——深化了先前拉丁美洲主教团会议中已有的一个主题——坚持认为,必须将边缘群体 视为能够创造自身文化的主体,而非慈善的对象。这意味着这些群体有权活出福音,依据其文化中所存的价值观来庆祝和传播信仰。贫困的经验赋予他们识别现实某些方面的能力,这是他人所无法看到的,因此社会需要倾听他们。对教会而言也是如此,她必须积极重视他们"民众性"的活出信仰的方式。阿帕雷西达最终文件中的一段优美文字帮助我们反思这一点,以找到正确的态度:"唯有那使我们成为朋友的亲近,才能让我们深刻体会当今穷人的价值、他们合理的渴望,以及他们特有的活出信仰的方式。……日复一日,穷人成为福传和整全人类促进的主体:他们在信仰中教育子女,在亲友邻舍间活出恒久的团结,不断寻找天主,并赋予教会朝圣之旅以生命力。在福音的光照下,我们承认他们在基督眼中拥有无限的尊严和神圣价值,基督如同他们一样贫穷,并在他们中间遭受排斥。基于这一信德的体验,我们将与他们一同捍卫他们的权利。"[110]
101.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优先选择穷人中有一个我们必须不断铭记的方面:这一选择确实要求我们"将关注放在他人身上……。这份充满爱意的关注是真正关心其人的起点,由此我愿切实寻求他的益处。这包含着珍视穷人本身的美善、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的文化、他们活出信仰的方式。真爱总是默观的,它让我们能够服务他人,不是出于需要或虚荣,而是因为他是美的,超越其外表……。只有通过这种真实而贴心的亲近,我们才能恰当地陪伴他们走解放的道路。"[111] 因此,我向所有选择生活在穷人中间的人致以诚挚的感谢;即那些并非偶尔前去探望,而是与他们同住、如同他们一样生活的人。这一选择理应在福音生活的最高形式中占有一席之地。
102.由此视角可见,"我们所有人都让自己被穷人福音化"[112],以及所有人都承认"天主愿意通过他们向我们传达的奥秘智慧"[113]的必要性,已清晰无疑。在极端的不稳定性中成长,学会在最艰难的处境中生存,怀着"再无他人认真对待他们"的确定感去信赖天主,在最黑暗的时刻彼此相助——穷人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将此珍藏于心灵的奥秘中。我们当中那些未曾经历过类似"处于边缘的生活"境遇的人,无疑可以从这源于穷人经验的智慧泉源中领受良多。只有将我们的抱怨与他们的痛苦和匮乏相比较,我们才可能接收到那邀请我们简化生活的责备。
参考文献
[76] 圣若望二十三世,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前一个月向全球信友广播讲话(1962年9月11日):《宗座公报》54(1962),682页。
[77] G. Lercaro,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卅五次全体大会上的发言(1962年12月6日),2号:AS I/IV, 327-328页。
[78] 同上,4号:AS I/IV, 329页。
[79] Istituto per le Scienze Religiose (编), Per la forza dello Spirito. Discorsi conciliari del Card. Giacomo Lercaro, 博洛尼亚 1984, 115页。
[80] 圣保禄六世,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二届会议隆重开幕时的讲话(1963年9月29日):《宗座公报》55(1963),857页。
[81] 同一位教宗,要理讲授(1964年11月11日):《保禄六世训导集》,II(1964),984页。
[82]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69, 71号。
[83] 圣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1967年3月26日),23号:《宗座公报》59(1967),269页。
[84] 参同上,4号:《宗座公报》59(1967),259页。
[85] 圣若望保禄二世,《社会事务关怀》通谕(1987年12月30日),42号:《宗座公报》80(1988),572页。
[86] 同上:《宗座公报》80(1988),573页。
[87] 同一位教宗,《论人的工作》通谕(1981年9月14日),3号:《宗座公报》73(1981),584页。
[88] 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2009年6月29日),7号:《宗座公报》101(2009),645页。
[89] 同上,27号:《宗座公报》101(2009),661页。
[90] 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团全体会议,《麦德林文件》(1968年10月24日),14, 7号:CELAM, Medellín. Conclusiones, 利马 2005, 131-132页。
[91] 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202号:《宗座公报》105(2013),1105页。
[92] 同上,205号:《宗座公报》105(2013),1106页。
[93] 同上,190号:《宗座公报》105(2013),1099页。
[94] 同上,56号:《宗座公报》105(2013),1043页。
[95] 同一位教宗,《祂爱了我们》通谕(2024年10月24日),183号:《宗座公报》116(2024),1427页。
[96] 圣若望保禄二世,《百年》通谕(1991年5月1日),41号:《宗座公报》83(1991),844-845页。
[97] 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202号:《宗座公报》105(2013),1105页。
[98] 同上。
[99] 同一位教宗,《众位弟兄》通谕(2020年10月3日),22号:《宗座公报》112(2020),976页。
[100] 同一位教宗,《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209号:《宗座公报》105(2013),1107页。
[101] 同一位教宗,《愿祢受赞颂》通谕(2015年5月24日),50号:《宗座公报》107(2015),866页。
[102] 同一位教宗,《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210号:《宗座公报》105(2013),1107页。
[103] 同一位教宗,《愿祢受赞颂》通谕(2015年5月24日),43号:《宗座公报》107(2015),863页。
[104] 同上,48号:《宗座公报》107(2015),865页。
[105] 同一位教宗,《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180号:《宗座公报》105(2013),1095页。
[106] 信理部,《关于"解放神学"的某些方面的训令》(1984年8月6日),XI, 18号:《宗座公报》76(1984),907-908页。
[107] 第五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主教团全体会议,《阿帕雷西达文件》(2007年6月29日),392号,波哥大 2007, 179-180页。参本笃十六世,在第五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主教团全体会议开幕工作会上的讲话(2007年5月13日),3号:《宗座公报》99(2007),450页。
[108] 参第五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主教团全体会议,《阿帕雷西达文件》(2007年6月29日),43-87号,31-47页。
[109] 同上,《最终文告》(2007年5月29日),4号,波哥大 2007, 275页。
[110] 同上,《阿帕雷西达文件》(2007年6月29日),398号,182页。
[111] 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199号:《宗座公报》105(2013),1103-1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