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入门——旧约概述(1)。连载9
发布日期:2025-11-27 | 作者:意鸣子圣经入门——旧约概述(1)。连载9
旧约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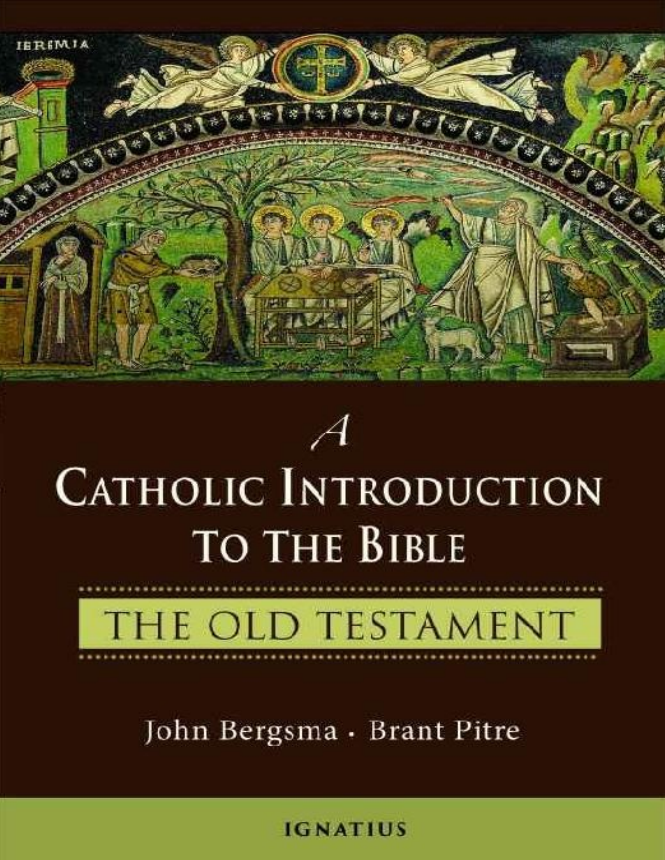
死海古卷
对于旧约文本学者而言,更受关注的是死海古卷。这是一批古代犹太图书馆的遗存——普遍认为属于被称为“艾色尼派”的群体——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死海西北端一个名为古木兰的地方的洞穴中被发现。死海古卷为我们提供了圣经任何部分的最古老抄本,包括可追溯至主前2世纪的文本。在死海古卷中,除《艾斯德尔传》和《乃赫米雅记》(即:《厄斯德拉下》)外,所有公认的旧约经卷都有抄本。然而,像《厄诺克一书》和《犹比勒书》(即:《禧年书》)这样的伪经,其数量比大多数圣经经卷都要多,且发现的《多俾亚传》抄本数量与《耶肋米亚》《厄则克耳》和《约伯传》相同(各有六份)。正因如此,如前所述,大多数学者认为艾色尼派所用的神圣著作集——即后来所谓的“正典”——比法利塞人和后来的拉比犹太教的正典范围更广。
在古木兰发现了约一千卷古卷的残片,其中约250卷是圣经经卷的抄本,几乎全部为希伯来文。在死海古卷中的希伯来文圣经文本里,约三分之一与我们现今所知的马所拉文本的形式极为接近。其他圣经文本在措辞上存在差异,其中一些与《七十贤士译本》高度一致(约占文本的5%;见下文关于七十贤士译本的内容),一些与撒玛黎雅人所用的梅瑟五书形式一致(也占5%),还有大量文本在许多圣经段落中有着独特的读法(措辞差异)。
死海古卷改变了学者们对旧约文本历史的看法。显然,在古代,约在耶稣时代,犹太圣经的文本在不同的希伯来文手稿间存在差异。随着时间推移,犹太拉比传统在马所拉学者的工作中达至顶峰,确立了标准的文本形式。马所拉文本大体上是一种古老且基本可靠的文本形式,但它终究只是古代流传的文本之一。
死海古卷中发现的与希腊文《七十贤士译本》高度一致的古代希伯来文圣经文本,也改变了学者们对《七十贤士译本》可靠性的看法。《七十贤士译本》中的某些经卷——最显著的是《耶肋米亚》和《撒慕尔纪上》——长期以来被认为与希伯来文马所拉文本存在显著差异。许多学者曾怀疑,《七十贤士译本》的译者因对希伯来文原文不够忠实,才造成了这些差异。然而,死海古卷表明,《七十贤士译本》的译者大体上是直接翻译他们面前的希伯来文。《七十贤士译本》与马所拉文本部分内容的显著差异,源于圣经经卷的希伯来文版本不同,而非《七十贤士译本》译者的翻译行为。
尽管对死海古卷的研究确实改变了学者们对圣经希伯来文文本发展的理解,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信徒(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所用的译本。古卷中发现的异文,对于专门研究文本批判(即研究圣经确切措辞)的圣经学者而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极具意义,但神学家和普通信徒往往对其兴趣不大。绝大多数措辞差异都无关紧要(少数词语的遗漏或增添、同义词的替换、词形或动词变位的变化);而在那些意义重大的差异中,通常很容易区分出原始读法与某些手稿中的错误或有意改动。
圣经文本与现代天主教译本
在1943年《由圣神嘘气》通谕发布之前,天主教的英文圣经译本皆以《拉丁文(通行)译本》为依据。庇护(比约)十二世阐明,脱利腾大公会议宣布《武加大译本》为“权威”译本,意在确立其作为官方拉丁文译本(在众多流传的拉丁文译本中)的地位,并为公开的神学讨论和教育提供统一的圣经文本。脱利腾大公会议的法令并非要将《武加大译本》置于圣作者所撰的原始希伯来文、希腊文或阿拉美文文本之上,赋予其更高权威。用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话说:
“若脱利腾大公会议希望‘众人皆以《武加大拉丁译本》为权威’,众所周知,这仅适用于拉丁教会及该圣经的公开使用;无疑,这绝不减损原始文本的权威与价值。因为当时所论的并非这些原始文本,而是彼时流传的拉丁文译本……因此,会议肯定《武加大译本》这种特殊的权威,或如人们所说的‘正统性’,并非出于批判层面的原因,而是因其在众多世纪里于各教会中被合法使用;通过这种使用,在教会过去及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它被证明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毫无谬误;因此,正如教会自身所见证和肯定的,在辩论、讲学和布道中引用它是安全的,无需担心出错;故其正统性主要并非批判性的,而是司法性的。
因此,《武加大译本》在教义问题上的这一权威,绝不妨碍——甚至在今日几乎要求——要么通过原始文本来佐证和确认这同一教义,要么在任何场合都借助这些原始文本,凭借它们,神圣经文的正确含义日益清晰明了。”(《由圣神嘘气》21-22)
在这份教宗的通谕发布后,现代天主教旧约的英文译本——如1966年的《修订标准版圣经(天主教版)》(RSVCE)或1970年的《新美国圣经》(NAB)——均以现有的最佳原始语言文本为依据。这通常意味着旧约的希伯来文经卷以马所拉文本为基础,并参考古代译本和死海古卷进行补充。《武加大译本》仍是天主教拉丁礼的官方版本,在某些地方,它代表了教会的权威解释传统,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当代旧约研究
铭记这些天主教传统中的原则,我们通过简要概述当代圣经研究方法,来结束本章关于释经的内容。在圣经学术研究中,这些方法通常被称为“批判”方法,尽管“批判”一词是中性的,仅表示“分析”。在下文当中,我们将阐述各种圣经批判形式的起源与实践,首先从无争议的“低级”批判(即文本批判)开始,进而介绍曾被称为“高级”批判、如今通常称为“历史批判法”的各个阶段。
文本批判
文本批判是对圣经的古代手稿进行细致比较与分析,目的是尽可能重建所研究的圣经文献的原始措辞。
由于人为错误,任何两份圣经的古代手稿(手写抄本)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文本批判试图通过对文本的仔细比对,纠正明显的错误,如拼写错误或用词错误;剔除文本中添加的内容,无论这些添加是无意为之还是出于神学动机;并补全文本中的缺漏,即缺失的词语、短语和章节。
早期教父们就已经开展了文本批判工作。奥利振是教父时代最伟大的文本批判家。他编撰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六栏圣经》(Hexapla),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旧约的希伯来文本、希伯来文的希腊语转写本、阿奎拉评注的《七十贤士译本》、叙马库斯评注的版本、他自己修订的版本以及狄奥多田修订的版本,分六栏排列。《六栏圣经》篇幅宏大,据说有五十卷之多,原本存放在凯撒利亚,直到主后7世纪穆斯林入侵时遗失。
中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困境阻碍了文本批判领域的诸多进展,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古典学术的复兴,促使人们重新努力出版原始语言的准确圣经版本。伊拉斯谟在16世纪初编撰了新约的批判文本。以在西班牙推动教会革新而闻名的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枢机(1436–1517),在16世纪赞助完成了文本批判领域的一项杰出成就——《康普鲁顿多语圣经》,这是一个包含希伯来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批判版本。旧约部分于1517年出版,其中《马所拉文本》、《武加大译本》和《七十贤士译本》以三栏并行的形式呈现。
在现代,旧约的文本批判主要包括根据其他语言的古代译本,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死海古卷中发现的犹太圣经希伯来文抄本,对马所拉文本进行细微调整。鲁道夫・基特尔是德国的一位旧约学者(1853-1929),或许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旧约文本批判家。他编撰的马所拉文本批判版本最终发展为《斯图加特希伯来圣经》,这是由德国斯图加特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标准希伯来圣经印刷版本,被世界各地的圣经学者和译者用作国际标准。
历史批判法的兴起
教父们研究圣经的基本方法在宗教改革时期依然有效。新教改革者们往往没有详细阐述释经方法,但他们认同这样一种范式,即高尚的生活、合理的哲学以及人文教育——尤其是语法、逻辑和修辞——对于解释圣经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然而,在类型学的使用上,改革者们开始与天主教传统分道扬镳,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1)一些注释者过度使用类型学,提出了牵强附会的类型学关联,使这种方法声名受损;(2)类型学解释常常被用来支持改革者所反对的“罗马”教义;(3)由于缺乏教会训导权,改革者们对承认圣经具有多重含义感到不安,他们寻求一种解经方法,当将其应用于特定文本时,无论由谁应用,都能始终得出相同的、单一的含义。
因此,改革者们越来越多地偏离圣经的属灵意义,转而强调字面意义以及理解这种意义所需的文学工具:掌握原始语言和文学,并且越来越重视历史研究。改革者们对文本的语法和历史层面日益关注,再加上哲学领域的新动向(例如:巴鲁赫・斯宾诺莎和勒内・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以及由于席卷欧洲的宗教战争导致人们对教会机构普遍失去信心,这些都推动了“历史批判法”的发展。这是一种研究圣经的世俗方法,在启蒙运动期间影响力日益增强,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在圣经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源流批判
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批判或“历史”批判在18世纪中叶随着源流批判的兴起而正式开始,源流批判旨在辨别圣经作者所使用的资料来源。文学线索——例如:使用独特的术语或名称,以及存在明显的“重复叙述”或相似故事的重现——被用来区分某一圣经经卷的不同(假设的)来源。
受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著作的影响,早期源流批判的实践者包括法国天主教徒、奥拉托利会(Oratorian)神父理查德・西蒙(1638-1712)和世俗医生让・阿斯楚克(1684-1766)。西蒙于1678年出版了《旧约批判史》(法文《Histoire critique du Vieux Testament》),主张梅瑟只撰写了“梅瑟五书”中的法律部分,后来的编年史家零星地添加了叙事内容,导致《创世纪》和《出谷纪》的部分内容出现了明显的重复叙述和重复现象。他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得到正统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认可。一代人之后,让・阿斯楚克试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通过分离出据信编撰梅瑟五书所依据的不同文献,来为梅瑟五书的可理解性辩护,以对抗理性主义批判者。根据对天主的不同称呼——希伯来语中的“雅威YHWH(“主Lord””)和“厄罗亨Elohim”(“天主/神God”),阿斯楚克将明显的重复叙述(重复的故事)、重复内容和不一致之处,至少分离为两种不同的文献,并以平行栏的形式排列。阿斯楚克认为,梅瑟本人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撰梅瑟五书的,而后来的编者将这些文献合并在一起,才造成了多玛斯・霍布斯(1588-1679)、斯宾诺莎以及其他怀疑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些看似不一致的地方。
|
学者 |
重要著作出版年代 |
贡献 |
|
让・阿斯楚克 |
1753 |
提出《创世纪》中有两种可通过神圣的名字“雅威(YHWH)”或“厄罗亨(Elohim)”区分的来源 |
|
约翰・戈特弗里德・艾希霍恩 |
1780 |
将阿斯楚克的观点应用于整部《五书》;完全摒弃梅瑟为作者的说法 |
|
威廉・维特 |
1805 |
确定《申命纪》为独立来源;认为没有文献早于达味时代 |
|
弗里德里希・布利克 |
1822 |
将来源文献的范围扩展到《若苏厄书》 |
|
赫尔曼・胡普费尔德 |
1853 |
将“厄罗亨典(Elohist,E)”分为两个来源(E¹和E²) |
|
卡尔・海因里希・格拉夫 |
1866 |
试图证明E¹是最后出现的来源 |
|
尤利乌斯・韦尔豪森 |
1877-1878 |
确定E¹为“司祭典(Priestly source,P)”,并按年代顺序整理出来源为JEDP(即雅威典、厄罗亨典、申命典、司祭典,是对《五书》文献来源的一种学术分类假设 |
虽然西蒙与阿斯楚克并未质疑梅瑟对五书的实质性著作权,但随着源流批判的发展,历史上的梅瑟对圣经前五卷的任何实质性贡献最终都被抹杀了。一批德国学者持续推进并发展阿斯楚克的来源分析,其中包括J.G.艾希霍恩(1752-1827)、威廉・德・维特(1780-1849)、弗里德里希・布利克(1793-1859)、赫尔曼・胡普费尔德(1796-1866)、卡尔・海因里希・格拉夫(1815-1869),最终还有尤利乌斯・韦尔豪森(1844-1918)。
源流批判通常被认为在19世纪末达到巅峰,当时尤利乌斯・韦尔豪森提出了经典的梅瑟五书“文献假说”。他的观点在欧洲主要大学的旧约学者中几乎形成共识,持不同意见者的声音则遭到压制或忽视。尽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训导权对这一假说持抵制态度,但从韦尔豪森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约一百年间,该假说在新教与世俗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也渗入天主教大学。
韦尔豪森提出的经典文献假说认为,梅瑟五书是由四个更古老的文献来源汇编而成。按照这一理论,“雅威源流”(因德语中“雅威”为“Jahwe”,故缩写为“J”)由一位犹大人(Judeans)于主前850年左右撰写,其几乎专用希伯来语中“雅威”(YHWH)这一名称称呼天主,内容包含关于列祖的朴素叙事,其中的天主具有鲜明的人性特质。约一个世纪后,“厄罗亨源流”(缩写为“E”)出现,是由北方以色列人所著,以更为疏离、正式的风格重述了许多“J源流”中的故事,所描绘的是一位超然的天主。主前650年左右,“申命纪源流”(缩写为“D”)撰写了《申命纪》的主体内容,为犹大约史雅(约主前650-610年)时期的宗教改革提供依据;在流亡时期(主前587-537年),该来源由其作者本人或后世编者与“J”“E”合并后的叙事结尾相融合。最终,主前5世纪某时,流亡后的犹大司祭们撰写了大量关于礼仪与道德的法律,构成《肋未纪》《户籍纪》的主体内容及《出谷纪》的结尾部分。依据这一理论,这些“司祭源流”(缩写为“P”)被置于核心位置,周围环绕着更古老的叙事,由主前5世纪或4世纪某位不知名的编者(缩写为“R”)整合在一起。这种基本形式的文献假说在旧约研究史上影响深远,本书后文将专门设一节对此进行探讨。
形式批判
19世纪末,韦尔豪森在源流批判领域的研究成果看似无懈可击,学者们遂开始探寻新的圣经分析路径。与韦尔豪森同时代的德国学者赫尔曼・冈克尔(1862-1932)较为年轻,他与旧约形式批判的发展紧密相关。形式批判(德语为“Formgeschichte”,即“形式的历史”)致力于识别并界定旧约文本中被称为“pericopes”(读作per-IH-koh-peez,意为段落)的独立文学单元的“形式”或体裁,进而为该单元确定一个可能与其起源相关的历史文化“生活场景”(德语为“Sitz-im-Leben”)。冈克尔认为,不同的文学体裁显然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社会背景(如王室宫廷、圣殿、部落篝火旁等)相对应,因此识别体裁是探寻某一段落起源时间与地点的关键。
并非偶然的是,冈克尔最具影响力的形式批判著作聚焦于《圣咏集》。《圣咏集》中构成诗集的各类赞美诗与歌曲的“生活场景”,往往可从附于圣咏的标题(咏45:“爱情歌”;咏120:登圣殿献祭时演唱的礼仪性“上行之诗”;圣咏本身的内容:咏2:王室登基圣咏、咏51:忏悔圣咏、咏69:为受迫害者所作的哀歌)中推断而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并非每一卷圣经都像《圣咏集》这般适合形式批判分析。
传统批判
20世纪中期,两位德国旧约学者格哈德・冯・拉德(1901-1971)与马丁・诺思(1902-1968)主导了该领域研究,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冈克尔的成果。这些学者超越形式批判,提出了“传统批判”这一研究方法。该批判方法关注旧约文本背后那些假定的原始口头“形式”的段落随时间的演变,尤其注重它们向书面形式的转变及被纳入更宏大圣经叙事的过程。因此,在德语中,这一方法更准确地被称为“Traditionsgeschichte”,即“传统的历史”。
将传统批判应用于梅瑟五书时,其不再强调源流批判者所提出的贯穿五书的四种文学文献,而是聚焦于最终文本背后的传统在口头阶段中,单个叙事或叙事块的假定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传统批判试图充当形式批判与源流批判之间的理论“桥梁”。
编辑批判
马丁・诺思还与旧约编辑批判的发展相关。“redaction”(编辑)一词源自德语“Redaktor”,意为“编者”。编辑批判(德语为“Redaktionsgeschichte”,即“编辑的历史”)研究的是将各个文本单元整合为如今圣经文本中所见叙事“最终形式”的编辑过程。尽管韦尔豪森等早期学者已运用过基本形式的编辑批判,但诺思凭借其对旧约历史书的编辑批判研究声名远扬。他认为,《若苏厄书》至《列王纪下》是由一位抄写员于主前7世纪或6世纪编辑整合而成,目的是强调以色列人的后裔必须坚守《申命纪》中记载的梅瑟盟约。自20世纪40年代诺思的著作问世后,学者们开始将《若苏厄书》至《列王纪》这些历史书称为“申命纪体历史”,以体现这种关于这些书卷最终形式的编辑批判结论。
综合历史批判法
源流批判、形式批判、传统批判和编辑批判通常被视为一种综合方法的重要步骤,这种综合方法现在被称为历史批判法或“历史批评”。这种方法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从研究文本来源开始,到最终编辑结束,以呈现文本创作的完整历史。用宗座圣经委员会的话来说:
当最后一种方法(编辑批判)]发挥作用时,历史批判法的整个一系列不同阶段的特征就完整了:从文本批判进展到文学批判,通过剖析工作来寻找文本来源(源流批判);然后转向对形式的批判性研究(形式批判),最后到对编辑过程的分析(编辑批判),编辑批判尤其关注文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圣经作者和编辑者的意图,以及他们传达给最初读者的信息。这些成果的取得赋予了历史批判法极高的重要性。
强调历史批判法的这种综合性特征是很重要的,因为归根结底,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一组旨在重构圣经文本最终形式背后历史的多种批判方法。在圣经研究中,“历史批判法”与古代历史学家可能使用的“历史方法”不同。就源流批判、形式批判、传统批判和编辑批判而言,历史批判法旨在重构的“历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文本创作的历史。这一点在德语对这些批判方法的描述中比在英语翻译中更为清楚。
从20世纪最后25年开始,学者们开始对自17世纪以来实践的历史批判法的各个方面提出质疑。一些学者指出,历史批判几乎完全关注文本的创作过程,而不是发现我们所拥有的文本的意义。这使得这种方法明显不完整,因为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推测文本的前期历史上,它往往无法达到释经的目标:揭示文本最终形式的意义。
其他学者指出,源流批判者使用的许多历史和文学假设往往是他们自己时代和文化的产物,应用于古代文献时是不合时宜的。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古代作者喜欢使用各种重复、对偶、张力和双关语,而现代源流批判者则认为这些是多种文学来源的无可争议的标志。尽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这些特征可能是多人创作或编辑不当的信号,但在古代文本中未必如此。
另一种批评与贯穿主要源流批判、形式批判和编辑批判作品的某些值得商榷的哲学和神学倾向有关。例如,几乎所有对历史批判法发展最有影响力的贡献者都是德国自由派新教徒。一方面,这一传统以其学术严谨性和对百科全书式详尽资料收集的偏好而广受赞誉。另一方面,许多犹太学者指出,自由派新教的某些偏见常常歪曲了这种方法的一些主要结论。
近年来,还有其他美国和欧洲学者认为,即使是威尔豪森(Wellhausen)的作品,在对来源的界定和年代判定上也不够激进。因此,当代对旧约,特别是对《梅瑟五书》的源流批判,处于一种激烈的争论状态,不同阵营在各种假设来源的存在和年代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
除了源流批判之外,形式批判和传统批判也成为了学术争论的主题。学者们对以下观点提出了质疑:仅仅通过体裁就能可靠地确定一个段落的生活背景(Sitz-im-Leben)和历史性,或者仅仅根据现存的书面文本就能自信地重构数百年或数千年前口头形式的发展。换句话说,形式批判和传统批判就其本质而言,是极具推测性的工作,因为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文本背后的形式和传统。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许多当代学者已经放弃了形式批判和传统批判,而那些仍然使用这些方法的学者也比前几代人更加谨慎。
最后,编辑批判——对最终编辑过程的研究——可能是在当代圣经研究的动荡中经受住考验最好的方法,因为与其他历史批判方法不同,它直接研究圣经文本的最终形式。然而,就其对各种作者和编辑选择背后的原因进行假设而言,编辑批判的某些方面在本质上也可能极具推测性,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作者或编辑的思维过程,只能从最终文本中推断原因。然而,由于它特别强调这种最终形式,编辑批判在许多方面与现在应用更广泛的共时性方法相似(见下文)。